
摘要:里森运用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论题学分析了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当中记载的21个学派争议,试图证明论题学是古典罗马法学家所运用的重要方法。同时,她以罗马法学、法律实践和论题学之间的三角关系为基础解释学派争议产生的原因。她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论题学的运用方式,但她所强调的论题学对罗马法学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得到证明,其理论也无法经受住检验。从论题学的运用方式来看,它也不适合为现代法学家使用。出于这个原因,菲韦格改造了西塞罗的论题学,同时在思维方式和技术两个层面上使用论题学的概念,并将"论题目录"修改为"观点目录"以维持其理论与古代论题学的联系。然而,经其改造的理论也未能为实践提供特别的帮助。总而言之,论题学(包括西塞罗的和菲韦格的)在现代法学中的实践意义,仍然无法得到证明。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菲韦格在1953年出版的《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Topik und Jurisprudenz:Ein Beitrag zur rechtwissenschaftlichen Grundlagenforschung)一书中声称,论题学对当代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本著作“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著作甫一问世即在德国学界引起反响,相关讨论持续长达20年之久,且迅速被译成多国文字刊行,有浩如烟海的评论和研究论文,至今仍属德国和欧洲许多大学法学研讨班以及国际学术会议的研讨主题之一”。该书由舒国滢教授翻译成中文。1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另一方面,现任教于荷兰蒂尔堡大学人文学院(Tilburg School of Humanities)的特萨·G·里森(Tessa G.Leesen)3于2010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盖尤斯遇见西塞罗:学派争议当中的法与修辞学》(Gaius Meets Cicero:Law and Rhetoric in the School Controversies,Leiden·Boston 2010)。在该书当中,她以罗马元首制前期两大法学派的争议为切入点,利用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论题学(topica)4详细地分析了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当中记载的21个学派争议,试图证明论题学是古典罗马法学家所运用的重要方法。里森的著作在欧洲法律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多期刊发表了有关该书的书评,其中有赞赏也有批评。5在我国,舒国滢教授和徐国栋教授通过相关论著,向学界介绍了里森的理论。
综合这两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论题学这种古老的法学方法,在古典罗马法中被广泛使用,并且对当代法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一种有两千年历史的法学方法将要焕发新的生命。这对于注重法学方法的人而言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然而,论题学是否真的可以为我们所用,仍然是有疑问的。首先,论题学的发展并不具有连续性。菲韦格在上述著作的开篇将论题学描述为“今天几乎不为人知”的学问。如果这种方法很实用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中断的情况呢?另外,就像徐国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里森所描述的古代罗马的论题学和菲韦格所说的“论题学”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7也就是说,存在两种不同的“论题学”。这不仅意味着菲韦格企图复兴的不是古代罗马的论题学,而且还引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论题学”?它们具体有何不同?哪一种才是真的?如果里森对古代罗马论题学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菲韦格误解了论题学?还是说,他也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而故意“误解”论题学?
由于论题学本身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问,所以上述疑问需要从实践的视角去解答。因此,本文的任务是,通过探讨这两种“论题学”的运用方式及其在相应背景中的实践意义,来解答上述疑问。根据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首先应考查古代罗马的论题学,然后再考查菲韦格的论题学。对于古代罗马的论题学,我们将不直接从西塞罗的论题学入手(因为舒国滢教授和徐国栋教授的著述和译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材料),而是在里森的理论框架中对其进行探讨。这样做反而更加有益,因为,一方面,里森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在其理论框架中可以对问题进行更为整体性的探讨;另一方面,里森的理论经过上述中国学者的介绍,已经为我国读者所熟悉,有必要在此指出其错误之处。因此,接下来我首先从里森的理论开始。
一、里森的论题学理论
里森用21个示例生动地揭示了论题学在古代罗马法私法中的运用方式。然而,我们对里森的理论尚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解。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里森的写作本身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另一方面在于,我们还没有对其理论进行一种批判性的检验。因此,有必要从其理论背景出发,全面考察里森的理论,并对其具体观点作出评价。这个工作虽然有些繁琐,但是对于正确理解论题学的运用方式及其在古典罗马法中的意义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里森理论的学术脉络
萨宾学派和普罗库鲁斯学派之间的争议对于现代罗马法学者而言,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很多现代学者认为,查清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有助于揭开古典罗马法取得辉煌成就的奥秘。
关于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哲学基础不同说”“保守和进步说”“方法论不同说”“政治立场不同说”和“无根本差别说”。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位学者可能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理论来解释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当然,“无根本差别说”和另外四种理论是不相容的。
“哲学基础不同说”的代表人物是索科罗维斯基(P.Sokolowski)和贝伦茨(O.Behrends)。索科罗维斯基认为,萨宾学派受到斯多亚学派的影响,而普罗库鲁斯学派则主要受逍遥学派的影响。8贝伦茨则认为,萨宾学派主要受斯多亚学派的影响,而普罗库鲁斯学派主要受怀疑主义的影响。
“保守和进步说”可以说源自古典罗马法学家彭波尼(Pomponius),因为他在《学说汇纂》(D.1.2.2.47)当中提到,“卡皮托坚持传授给他的东西”(Ateius Capito in his,quae ei tradita fuerant,perseverabat),而“拉贝奥进行了大量创新”(Labeo……plurima innovare instituit)。因此,一些现代学者,比如,福格特(M.Voigt)、科德雷布斯基(J.Kodrebski),认为萨宾学派和普罗库鲁斯学派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保守的,后者是进步的。10比较有趣的是,另一些学者,比如,卡洛瓦(O.Karlowa)、法尔奇(G.L.Falchi),正好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即认为萨宾学派是进步的,普罗库鲁斯学派是保守的。
“方法论不同说”的支持者非常多,包括迪尔克森(H.E.Dirksen),昆策(J.E.Kuntze),斯坦因(P.Stein),利普斯(D.Liebs),赫尔伯格(M.Herberger),斯卡凯迪(M.G.Scacchetti)和法尔奇等。最早提出方法论不同说的应该是迪尔克森,早在1825年他就提出,萨宾学派和普罗库鲁斯学派的对立在于方法论上的不同。12后来该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罗马法学者斯坦因。对于斯坦因而言,彭波尼作为学派争议时代的法学家,其论断不能完全被无视,但是彭波尼也没有明确说拉贝奥是在法律学说上具有创新性,因此他说的创新更有可能是指法律方法和法律技术方面的。斯坦因通过分析《学说汇纂》当中收录的拉贝奥的观点来重构其法律方法,并比照对立学派的观点,从而得出两大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差异:(1)拉贝奥对词义的解释(interpretatio verborum)非常感兴趣,并在解释词义时倾向于字面的、客观的解释,而不考虑文字作者的主观意图。(2)在法律适用有疑问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普罗库鲁斯学派处理案件的技术方法比较丰富。(3)拉贝奥比起之前的法学家,更加注重精确的定义和区分。(4)两大学派在方法上的不同反映了古希腊两大语法学派———规则派和异常派(analogists and anomalists)之间的对立。规则派认为语言天生就是有规则的,并努力去证明名词和动词可以根据形式的相似性划分为不同的变格和变位类型。异常派则认为语言不存在一般原则,规则派提出的规则都存在大量的例外。斯坦因认为,拉贝奥主要受规则派的影响。
“政治立场不同说”认为普罗库鲁斯学派反对皇权制度,萨宾学派支持皇权制度。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拉贝奥在政治上反对奥古斯都,卡皮托是奥古斯都的支持者。但是,两大学派后来的领袖并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因此这个理论今天有点过时了。
“无根本差别说”认为,两大学派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不存在一个可识别两大学派法学家立场的明确标准。这种理论首先是施拉德尔(E.Schrader)和布雷默(F.P.Bremer)提出的,然后得到了佩尔尼斯(A.Pernice)和巴维耶拉(G.Baviera)的进一步完善,乔洛维茨(H.F.Jolowicz)和瓜里诺(A.Guarino)也表示赞同。其中,巴维耶拉的阐述最为详尽。14这种理论首先否定彭波尼的论断,其次,倾向于把“两大学派”说成是“两大学校”,认为它们是教学机构而不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圈子。
在前述五种理论当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占据优势地位。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相互都无法说服对方。里森认为,现代文献无法令人信服地解决学派争议的问题,而且它们存在着双重缺陷:方法论上的缺陷和实质上的缺陷。
在方法论上,很少有现代学者愿意花力气去对主要原始文献进行系统、彻底的分析,他们注重的是罗马私法的教义学方面,而忽视了理解现实法律问题及争议背景的重要性。因此导致了三个不利的结果:(1)现代理论大多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之上,而无法找到原始文献的支持;(2)盖尤斯提到的论证理由被忽视;(3)一些学者甚至明确拒绝盖尤斯提供的论证理由。
实质上的缺陷在于,现代文献往往以两大学派之间存在根本性理论对立为出发点,以以下三个假设为前提:(1)假设所有的学派争议都可以用单一的理论去解释;(2)学派之间的对立是根本性的,而且是一贯性的;(3)学派存在内在的一贯性。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1)每一种理论都只能解释一小部分学派争议,而无法解释全部或者大部分学派争议;(2)学派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对立;(3)学派并不存在内在一贯性。比如,拉贝奥和普罗库鲁斯之间也会产生争议。
然而,里森并不是反对上述全部理论。她的理论立场非常明确:自始至终都认为两大学派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各自不存在一贯的理论。也就是说,里森持“无根本差别说”,而不是“方法论不同说”。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里森眼里,两大学派所使用的方法正好是相同的,即都使用了论题学。里森肯定了巴维耶拉所阐述的“无根本差别说”,认为巴维耶拉正确地把学派和解答权联系在一起,但也认为巴维耶拉的理论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认为学派争议主要是教学观点上的争议,忽略了争议的实践方面内容;(2)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原始文献当中存在这么多学派争议,为什么学派争议显得这么重要。
(二)里森的主要观点
既然采纳了“无根本差别说”,那么学派争议的问题对里森而言就是学派争议存在之原因(raison d’être)的问题。里森的观点可以简单归纳如下:在法律实践当中,当某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需要寻求法律建议的时候,就出现了作为争议之基础的法律问题。因为两个学派的领导者都享有公开解答权,他们的解答都具有皇帝授予的权威性,因而对法官具有约束力。因此,如果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一个学派的领导者寻求法律建议,而另外一方当事人向另一个学派的领导者寻求法律建议,那么就会产生一项学派争议(因为各自都会作出有利于其顾客的解答)。显然,两大学派的领导者为了使其解答具有说服力,都需要适当的论证。为此,他们利用了修辞学和论题学。解开学派争议之谜的两把钥匙是:(1)罗马法学和法律实践之间的联系;以及(2)罗马法学和论题学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罗马法学、法律实践和论题学之间的三角关系为解释两大学派的存在及其争议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在论述第一把钥匙(即罗马法学和法律实践之间的联系)时,里森加入了解答权的因素。她区分一般争议和学派争议:当不同的法学家对同一个案件给出不同的解答时就会产生一般争议,而只有享有解答权的两个学派领导者就同一个案件产生的争议才能称为学派争议,当然,这两类争议在内容上并无不同。这个区分来自特勒根(J.W.Tellegen),19他认为享有解答权的学派领导者作出的解答因为对法官具有约束力,所以这种争议更加重要。他的实质性观点是,解答权和学派争议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里森在这里原版照搬了特勒根的观点。
在论述第二把钥匙时,里森强调,罗马法学家是非常熟悉修辞学和论题学的,而且论题学对罗马法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法律史学者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西塞罗的《论题学》对于罗马法的智识形成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然而,里森认识到,论题学主要服务于论证,而不是得出结论。因此,仅仅说明罗马法学家熟悉修辞学和论题学还不够,还需要为罗马法学家的结论找到来源。为解决此问题,以便论题学可以派上用场,里森大胆地提出,法学家在接受咨询时会给出有利于其客户的咨询意见。也就是说,法学家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取决于向其咨询的客户是哪一方当事人。有了结论之后,法学家会运用论题学的方法来为其结论寻找具有说服力的论据。
在论述完学术争议现状和这两把钥匙之后(导论部分),里森将该书的主要篇幅(第1—21章)用来分析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当中记载的21个学派争议,试图证明罗马法学家运用了论题学。在讨论完21个争议问题之后,便到了全书的结论部分。可以说,证明罗马法学家运用了论题学才是该书真正的主题。
对于每一个学派争议,里森分别用一章进行分析。在每一章当中,首先讨论相关的盖尤斯文本以及所涉争议(有时除两大学派的观点之外,还会有第三种观点);接着,分析关于该争议的现代理论;然后,利用论题学,分别重构两大学派在此争议当中采用的论证过程。在很多章的最后,还有一节专门探讨争议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其中的焦点是对两大学派论证过程的重构。下面我们以第一项学派争议为例,看看里森的重构。
第一项学派争议来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第一卷第196段(Gai.1,196):“男性从成为适婚人开始免除监护。然而,萨宾、卡西乌斯和我们的其他老师认为,适婚人,是指身体状态表明其已经性成熟的人,也就是说,能够生育的人;然而,对于不能性成熟的人,比如阉人,则应当考虑人们通常成为适婚人的年龄;然而,对立学派的权威们则认为应当根据年龄来判断是否适婚,也就是说,判定已满14周岁的男性为适婚人……”
争议的问题是,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个男性是否为适婚人,因此可以不再受监护。里森认为,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即对男性适婚人的定义,而萨宾学派和普罗库鲁斯学派都运用论题学来形成其意见并建构一个适当的定义。西塞罗的《论题学》(5.26—5.29)提供了几种定义的方法,里森认为两大学派都运用了5.29当中提到的方法来对男性适婚人下定义,所不同的是,在论证时,普罗库鲁斯学派运用了“相似论题”(locus a similitudine),而萨宾学派运用了“不同论题”(locus a differentia)。
普罗库鲁斯学派的论证如下:
(1)因为女孩和男孩都是人类,且确定女性是否成为适婚人的标准是年龄,
(2)所以,同样的标准应当被用来确定男性适婚人。
(3)某人达到某个年龄(也就是说,达到了14周岁),
(4)因此,他成为适婚人。
萨宾学派的论证如下:
(1)尽管男孩和女孩都是人类,但是确定男性适婚人的标准和确定女性适婚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因此,确定女性适婚人的标准———年龄,不应适用于男性。
(3)某人是男性,
(4)因此,年龄的标准不应用来确定他是否成为适婚人。
(三)里森理论的缺陷
里森对现有理论提出的批评很多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其对两大学派的论题学论证过程的重构也富有启发性,其对21学派争议的深入研究也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然而,她的主要观点、论证细节以及该书的整体逻辑都有可商榷的地方。
第一,在论证第一把钥匙时,关于解答权的部分存在问题。根据“无根本差别说”,学派仅指“学校”,那么学派争议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无法与学派争议在法源当中的显著地位相称。里森在这里提出解答权,认为学派争议均产生自享有解答权的两大学派领导者之间,而且产生自他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真实案例(显然解答权必须和实践联系在一起才具有足够的重要性)。这样既很好地解决了学派争议的重要性问题,也为解释学派争议产生的原因铺平了道路。但是这样同时也引起了诸多问题:首先,学派争议和解答权之间的联系缺乏证据支持。特勒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推测学派争议和解答权有关:22(1)彭波尼在讨论学派争论的中间提到解答权,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2)唯一可以确定享有解答权的人是萨宾,正好是学派的领导者;(3)格里乌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有提到“stationibus ius publice docentium aut respindentium”,这里的“stationes”很有可能是指两大学派;(4)解答权产生和消亡的时间和学派的产生消亡时间大体一致。可以说,这些理由非常牵强。其次,里森也承认,除了萨宾之外,根本无法确定哪些法学家获得了解答权,哪些法学家没有获得解答权。因此,“所有学派争议都是有解答权的学派领导者之间的争议”的说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根本就是不可证明的。再次,为了说明学派争议的重要性,必须把解答权和实践联系在一起,所以里森提出所有学派争议均产生自学派领导者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真实案例。然而,里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某些案件并非源自实践(第324页)。法学家对案件发表意见的可能性很多,不一定都是在实践当中遇到的案件,案件可能是前人留下的,可能是在教学当中想象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从同时代的其他法学家的著作当中看到的。最后,里森认为,两大学派的领导者都有解答权,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议最终只能由皇帝来解决,但是实际上不仅不能证明所有的学派争议最终都由皇帝解决,有些争议看起来也不像是由皇帝解决的。而且,在讨论关于加工的争议(第三项学派争议)时,里森明确指出,法官可以寻求一种折中意见(media sententia)(第89页)。
第二,里森大胆地认为,古罗马法学家会作出有利于其顾客的咨询意见(第309,第323页),但完全没有试图为此提出证明。这样简单直接地解决了学派争议产生的原因问题。对于罗马法学方法上最重要的问题,即罗马法学家是如何得出结论的,里森的回答是,这取决于来咨询的是哪一方当事人。如果古典罗马法学家都是这样得出结论,而不是带着一种在个案当中寻求公正的精神去处理案件,那么很难想象,罗马法学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里森把法学家等同于演说家(相当于古罗马的律师),认为他们都是为自己的顾客服务的。然而,古罗马法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服务,是无偿的,来咨询的当事人严格来讲不能算是其顾客。实际上,里森可能没有意识到,她自己就举出了相反的例证:一位市民向普布利乌斯·克拉苏(Publius Crassus)咨询时,后者给出了不利于该市民的意见(第21页)。而且,在争议涉及几代法学家时,就没有办法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来解释争议产生的原因。为了说明学派并不存在内在一贯性,里森指出,普罗库鲁斯学派内部也存在争议,比如,拉贝奥和普罗库鲁斯之间的争议;萨宾学派之间也会存在争议,比如,萨宾与一个世纪之后的尤里安和塞克斯图斯(Sextus)之间的不同意见(第315—316页)。为什么一个世纪之后同一个学派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呢?难道是有相对方的当事人来咨询尤里安和塞克斯图斯吗?还是说,他们在阅读完萨宾的著作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显然,后一种说法更可信。
第三,里森无法证明,罗马法学家确实运用了论题学。里森详细地分析了21个学派争议,试图证明罗马法学家运用了论题学。然而,其证明并未取得成功。首先,论题学是一套系统的理论,任何论证都可以通过论题学来解释。24也就是说,任何论证都可以被解释成运用了论题学。否则的话,论题学作为一套系统的论证理论就是失败的。西塞罗为了说明论题学的运用,在其《论题学》当中举了很多市民法的例子。很显然,那些市民法的例子在其写作《论题学》之前就已经存在,而西塞罗写作该书的缘由是,著名的法学家特雷巴提乌斯(C.Trebatius)头一次看到论题学这个词,很想知道其内容。这意味着,在西塞罗的《论题学》之前,罗马法学家普遍还不知道论题学,但是西塞罗却可以用论题学来解释市民法。其次,未运用论题学进行的论证,也可能看起来像是运用了论题学。里森认为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和西塞罗的《论题学》在很多地方用语上非常相似。同时她也指出,西塞罗提到法学家经常在解答当中使用这样的词语(第320页)。这正好说明,西塞罗还没写《论题学》之前,罗马法学家就使用这样的词语了。就像普拉切克(Platschek)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要读过西塞罗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学才能得到“马就是马”的论证吗?25因此,可以说,里森无法证明,罗马法学家运用了论题学。论题学对罗马法学的影响有多大,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四,个别论述具有误导性。里森在导论部分提道:“更准确地说,当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们使用论题学论证而得出不同结论时,学派之间的争论也就产生了。”26当然,对于这一点,里森只是存在写作上的疏忽,她对论题学的作用的认识还是非常准确的。
第五,许多细节缺乏原始文献的支持,并缺乏论证深度和逻辑。以前述关于适婚人的学派争议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里森所重构的论证实质上是一种表面的论证,没有涉及根本性的论据,即为什么男孩和女孩相同或者不同?萨宾为什么认为男孩要通过检查是否性成熟来判断是否为适婚人?女孩又为什么要通过年龄来判断是否为适婚人?而且,比较严重的论证缺陷是,里森没有解释,为什么两大学派都要以女孩而不是男孩为推论基准?古代罗马社会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性的地位显然不如男性,而且,女性达到适婚年龄的意义也不如男性大,因为女性达到适婚年龄之后仍然会受到监护。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男孩很早以前就是通过身体检查来确定是否为适婚人,但是检查女孩的身体被认为有伤风化,所以女孩按照年龄来确定是否为适婚人。此外,里森可能没有意识到,其所重构的普罗库鲁斯学派的论证过程包含一个矛盾:既然普罗库鲁斯学派采用“相同论题”进行论证,其结论为男孩和女孩应该相同,那么为什么女孩的适婚年龄是12岁,而男孩却是14岁呢?
在关于要式物的学派争议当中,里森的重构也存在问题。该争议来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第二卷第15段(Gai.2,15):“然而,我们说那些通常会被驯化的动物是要式物。......认为它们自出生时起就立即是要式物。然而,涅尔瓦、普罗库鲁斯以及对立学派的其他作者则认为它们只有在被驯化之后才是要式物;如果因为太过野性而不能被驯化,则在达到通常会被驯化的年龄之后才被视为要式物。”里森认为,普罗库鲁斯学派在此运用了“词源论题”(locus ex notatione)。其论证过程如下:(1)因为要式物(mancipi)源自“用手抓”(manu capere),其含义是“掌控”,(2)所以,“要式的动物”(animalia mancipi)的定义必须包含着被驯化的要件(没被驯化就无法掌控);(3)小马驹还没有被驯化,(4)所以它不属于“要式的动物”这个概念。里森完全不提这段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因为太过野性而不能被驯化,则在达到通常会被驯化的年龄之后才被视为要式物。”显然,这句话无法通过“词源论题”来论证。
在讨论关于加工的争议时(第85页),里森认为,普罗库鲁斯学派的法学家借用了昆体良的表达(Inst.Or.,5.10.74):“Quod quis non habuit,non perdidit”(某人不能失去他从未拥有的东西)。但她没有注意到,该争议的一方———涅尔瓦(Nerva),在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Institutiones Oratoriae)一书出现之前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不可能看到这本书。27
(四)论题学在古典罗马法中的运用方式和实践意义
学者们喜欢从结果来推断罗马法学家在处理案件时运用了论题学,28但是很少有人反过来探讨,罗马法学家在遇到一个案件时,如何运用论题学。里森提供了论题学的一个大概的运用程序:论题学提供了一份有序排列的论题清单(checklist)以及从其中每一个论题获得论证的方法。在运用时,可以快速地从头到尾浏览一遍这份清单并找到所需的论证(第34,第84页)。也就是说,应该存在一本《论题学手册》,上面按照一定的顺序详细而完整地列着所有的论题,并且对于每个论题都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在我们了解了所要处理的案件的案情之后,应该打开这本手册,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全部论题,根据该论题的说明书,逐一思考哪个论题有形成合理论证的可能性。在选定一个论题之后,再根据说明书进行论证。对于古罗马的演说家来讲,这本手册也许是一件非常便利的小工具。受过修辞学训练的演说家,尤其是负责出庭诉讼的代理人,其结论通常是确定的,需要做的仅仅是对结论进行论证。因此,论题学在理论上是非常适合他们的。29但是,对于法学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论证,而是如何找到适当的结论。也就是说,如何处理案件才是最重要的。按照西塞罗在其《论题学》当中的说法,论题学并不服务于获得结论的目的。
那么,罗马法学家是如何获得结论的呢?按照里森的说法,他们可能是根据当事人的利益来确定结论的。但是,我们认为,他们总体上是独立、自由地获得结论的。正是这种独立和自由对于古典罗马法的成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罗马法学家获得结论的方法,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卡泽尔(Max Kaser)认为,罗马法学家的法发现(Rechtsfindung)主要依靠直觉(Intuition),正确判断的获得主要依靠某种直接的理解(ein unmittelbares Erfassen);这种对正确解决方案的本能觉察(spontane Erschauen)以确定而精致的法律事物感(juristische Sachgefühl)和丰富的经验为基础。30
因此,可以说,论题学对于罗马法的意义不像里森所说的那么大。罗马法学家是不是真的运用了论题学的方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了论题学的方法,仍然是有待证明的问题。
(五)小结
罗马法学家的方法论和两大学派的争议,对于罗马法学者而言,是两个历久常新的主题。现代学者在有限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去对历史进行重构。一种重构尝试是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现有证据的矛盾程度以及推测的合理性。总体而言,里森的理论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也缺乏原始文献上的证据,因此需要我们谨慎地去对待。论题学对于罗马法学的意义,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过,里森的重构虽然有诸多疑点,但仍然非常富有启发性,尤其是她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探讨论题学在罗马法当中的实践运用。
尽管里森过分强调了论题学对罗马法的意义,并且其解决学派争议问题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她对论题学本身及其运用方式的理解是基本正确的,至少可以说是符合西塞罗所述的论题学的。然而,这样的论题学对于现代法学家而言,可能意义并不大。甚至在菲韦格的著作出版之后,也没有人能证明它的作用。如果有人根据西塞罗的《论题学》和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制作一本论题学手册的话,我相信,在我们现代人当中,很少有人能正确地使用它。我们甚至不觉得它有什么用处。我们更习惯于通过考察案情当中的相关要素来形成论证,而不是通过检查论题清单来挑选论证。相信菲韦格在面对西塞罗的论题学时,也有同感。
二、菲韦格的论题学
舒国滢教授在为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一书写“代译序”时指出,“据菲韦格自己介绍,其写作此书,是受维柯于1708年所写的一篇教授演讲词透现的古代思想价值的激励,追寻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学问足迹,试图恢复‘现已无人知晓的’论题学之本真面貌及其与法学之间的关系”。31这个说法是有疑问的。菲韦格所说的“今天几乎不为人知的论题学”(die heute fast unbekannte Topik)是指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题学,他在该书第二章对其进行了探讨。从该章的内容来看,菲韦格对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题学的理解基本没有偏差,但他在后面的章节中所描述的“论题学”已经严重偏离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题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这种偏离,他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这种偏离是他故意而为,他并不是要恢复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题学,而是要建立自己的论题学。那么,菲韦格为什么要对论题学进行改造呢?答案很有可能在于,他跟我们持有相同的观点:古代的论题学无法为我们所用。显然,如果古代的论题学很好用的话,他可以直接使用或者稍微进行一些修改便可使用,而不需要将其改得面目全非。接下来,我们来考查菲韦格的论题学和西塞罗的论题学之间的差异。32
(一)从“论题目录”到“观点目录”
菲韦格认识到,“此后经过若干世纪所使用的论题目录表现出多少有些巨大的差别......在主要方面,后世看起来相当程度地紧随西塞罗,只不过,人们努力把他的分类表述得更清晰一些”。33从其具体论述来看,他对西塞罗的论题目录的理解基本没有问题。34但接下来,他说,“但我们必须稍微更为宽泛一些来把握概念,以便在整体上理解这里所谈及的思想。因为不仅仅存在着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及其追随者所论述的可以普遍应用的论题,而且也存在着一些适合于特定专业的论题”。所谓的适合于特定专业的论题(专用论题),是指“在一定的专业领域经常反复出现并已得到证实的观点”。35比如,就法学领域而言,《学说汇纂》第50卷第17题收录的古代法规则(包括法谚)便是专用论题。在这里,他引用了罗德里希·冯·施廷琴的《德国法学史》36和马修斯·格里巴尔多斯·穆法的《论学习的方法及策略三卷》37,并指出E.R.库尔修斯也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论题。38这说明,这样的变化并不是菲韦格自己首创的。39
实际上,菲韦格所做的并不是扩大论题的范围,而是偷偷地把西塞罗的“论题目录”改为“观点目录”。这点可以从他对“一阶论题学”和“二阶论题学”的区分中清楚地看出来。所谓“一阶论题学”是指,当人们遇到一个问题时,可能会尝试性地任意选择多少有些随机的观点;而当人们从一个经常备用的“观点目录”中去选择观点时,就属于“二阶论题学”。40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观点目录”。无论是“一阶论题学”,还是“二阶论题学”,都没有提及“论题目录”。这意味着,西塞罗的“论题目录”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41同时也意味着,菲韦格所述的“论题学”跟西塞罗的论题学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二)从论题学到问题思维
菲韦格对西塞罗的论题学进行的第二项改造是,把一种寻找论据的技术提升为一种思维方式。虽然他把论题学定义为“是由修辞学发展而来的问题思维技术”,42但他所描述的论题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所谓的“问题思维”。这种所谓的“问题思维”是在与“体系思维”相对立的语境中提出的,似乎一切不属于“体系思维”的东西都可以归入“问题思维”的名下。这样使得菲韦格可以毫无顾虑地把决疑法等同于论题学,43甚至把瓦尔特·威尔伯格所提出的动态体系论44作为当代民法学之论题学结构的一个例证。45将一种具体的方法或技术作为论题学的例证,这正好说明,论题学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技术或者法学方法,而是属于更为宽泛的思维层次的东西。
这里说的“体系思维”,实质上是指概念法学的思维。可以说,自从耶林以来,对概念法学的批判就没有停止过。20世纪出现的思潮(自由法运动、利益法学等)几乎都把概念法学或者体系思维作为批判的对象。简而言之,“体系思维”在面对问题时,所要做的是在体系当中为问题找到正确的位置,一旦其正确的位置被找到,问题便可以解决;如果体系当中没有其正确的位置,那么该问题便是体系当中无解的。作为其对立面的“问题思维”的具体含义是很难确定的。比较明确的是,它是“体系思维”之外的东西。因此,决疑法很容易被等同于“问题思维”。实际上,决疑法本身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它仅仅是指一种个案研究的方法,罗马法学者通常把它和“体系思维”相对立。如此一来,“论题学”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宽泛的思维方式。
(三)运用方式:从寻找论据到法发现
然而,菲韦格同时也在法技术的层面上使用其“论题学”。至于这种“论题学”具体应如何运用,菲韦格自己没有进行清晰的描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著作当中窥知一二。首先,需要有一个“观点目录”。当然,只有所谓的“二阶论题学”才需要一个“观点目录”,而“一阶论题学”看起来没有讨论的必要。就像菲韦格自己所说的那样:“论题学收集观点,最终将它们汇总成为目录,这个目录并不受演绎推导关联结构的左右,因此特别容易扩充和补充。”46其次,通过搜寻和把握一些观点,就可以针对某个问题复合体提出和思考一些答案。最后一步应该就是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对运用过程的描述虽然有些隐晦,但大体上是可以理解的。简单说,就是把“观点目录”作为一种经验予以参考,并进行判断,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一种“论题学”看起来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做的吗?唯一特别的地方是所谓的“观点目录”。但我们又无法从其现有的论述中查清:到底应该如何收集观点?又应该如何将收集到的观点编成“观点目录”?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清晰的回答,那么菲韦格的论题学在技术层面上便无法运用。如果仅仅是像《学说汇纂》第50卷第17题那样收集古代法规则或法谚,或者按照更为合理的顺序将其进行排列,那么这样的“观点目录”相较于民法典而言又有何优势呢?
如果说上述运用过程比较隐晦的话,那么拉伦茨提供了一个简单清晰的表述:论题学是,一种与个案结合的讨论程序,也就是,以获致参与讨论者之合意为目标,面对环绕个案周遭的所有问题一并予以讨论的程序。47这样一种程序本质上是通过详尽的讨论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的过程。这乍一看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讨论程序,但实际上也同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甚至都称不上一种技术。它为我们提供的指示只有一个,即讨论。
拉伦茨描述的“论题学”和菲韦格的“论题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显著差异,即前者已经完全忽略了“观点目录”,取而代之的是参与讨论者的观点。如果说,菲韦格通过把“论题目录”修改为“观点目录”,保持与古代论题学的一种联系,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用论题学的名称;那么,拉伦茨所描述的讨论程序已经完全与古代论题学断绝了联系。无论如何,菲韦格的“论题学”和拉伦茨所描述的“论题学”,都可以服务于得出结论,也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法发现的方法或者程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也已经远离了西塞罗的论题学。
(四)小结
我们可以看到,菲韦格故意对西塞罗的论题学进行了改造,并且同时在思维和技术两个层面上使用论题学这个名称。如果菲韦格仅仅把论题学视为一种问题思维,那么他的理论便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他必须在技术层面上使用论题学,使其具有特殊性和可操作性。他通过把“论题目录”修改为“观点目录”的办法,维持其理论与古代论题学的联系,从而增加其理论的吸引力。然而,他没有明确提出收集观点并汇编成“观点目录”的方法,所以他的理论在技术层面上面临着运用上的困难。总体而言,菲韦格的“论题学”在法学中的实践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可以说,菲韦格的理论改造并没有取得成功。
至此,我们已经详细考查了里森和菲韦格的理论。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我们也探讨了西塞罗的论题学和菲韦格的“论题学”的运用方式。在今日之法律实践当中,我们很难说它们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可以说,在我国的民法学当中,占主导性地位的仍然是体系性思维。其他的方法、技术或者思潮如果不与体系性思维完全对立起来,而是承担起一种辅助、检验或纠正的功能,那么对于法律实践而言,也许更有益。
注释:
[1]舒国灌︰《走近论题学法学》,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4期,第11页。
[2]出现了大量关于论题学的论文,新近的如何卫平:《论题学与解释学》,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7-37页﹔韩振文︰《论题学方法及其运用》,载《法律方法》(第21卷),第244-254页;高伟伟︰《在"开放体系中论证".-论题思维的作用与限度》,载《法律方法》(第18卷),第90-103页;高伟伟︰《法律论证之论题学进路》,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4期,第54-62页。
[3]徐国栋教授根据荷兰语读音将其姓氏翻译为"雷森"。
[4]topica"被我国学者翻译为"论题学""地方论""类观点学"等。关于论题学的基本问题,请参见舒国灌︰《论题学︰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载《研究生法学》2011年第6卷,第1-37页;徐国栋︰《地方论研究∶从西塞罗到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西塞罗的《论题学》已有中文译本,见西塞罗︰《地方论》,徐国栋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秋合卷,第1-25页。
文章来源:柯伟才.论题学的运用方式及实践意义——评里森和菲韦格的论题学理论[J].南大法学,2021(04):1-14.
分享: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发挥着特有的制度优势。由于我国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公众对此缺乏了解,促使公众深入了解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基本知识和政策成为关键因素。通过强化政府部门的宣传力度、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宣传机制的建设、加大新闻媒体宣传以及普及医学知识。
2022-03-1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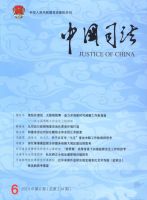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主要阵地,是依法治国落实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方式手段,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法治保障作用、德治教化作用、自治强基作用以及智治支撑作用,完善相关法律问题。
2022-03-04
在司法保护实践中,知识产权维权案件具有周期长、举证难、赔偿低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惩罚性赔偿立法,经历了早期部门立法、政策推动、立法完善三个阶段。它在司法审判、保护创新方法,有正面意义;同时,它存在立法层级不统一、保护手段单一、惩罚程度偏低等不足。期待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立法,使用多元保护机制,以案例指导审判。
2021-10-29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除去刑法中有规定的外,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的,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四个条件分别为:未经相关依法批准;公开形式向社会宣传;承诺一定时间归还本金、利息或是给予相应回报;针对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2021-10-21
2020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基本勾勒出我国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适用情形、责任主体及具体矫治措施,调整和修改了原矫治措施中已被废止或在实践中难以得到适用的内容,意味着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迈向了新阶段。但现有的修订内容依然在部分问题上未作有效回应,针对专门教育矫治措施的适用对象混同、适用程序相对粗糙,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构成与定位同其权责内容的非统一性,部分规则内容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不当等问题均会对随后的立法施行带来实质影响。
2021-09-23
从技术特点来看,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式的技术架构,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比特币价格急剧变动的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受到了诸多的关注。近年来,在我国相关发展战略、优惠政策等大力支持下,使得区块链技术的适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在传统工作中,区块链多是集中在货币、金融等相关性领域。近几年来,已经深入拓展到了社会治理领域中。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正视到区块链技术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优势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其中所存在的弊端。在区块链的应用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导致其积极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甚至
2021-08-30
《民法典》关于婚姻家庭的规定表明,家庭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基础意义。但法律实践面对着如何安顿家的棘手难题,作为家庭之价值基础的孝道与现代法治也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回应这个难题,需要清楚界定家庭与孝道在结构上的重叠和价值上的整合关系。法律语境下的家庭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两种结构,以及立法克制与司法建构双轨的公共道德面向。
2021-08-28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夫妻财产制类型。有效厘定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构成要素并总结过往的司法适用经验,对《民法典》生效后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条件要素的厘定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基础;时间要素的厘定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价值实现的时间维度;方式要素的厘定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意思自治实现的前提;标准要素和形式要素的厘定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落实的保障;司法适用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运行的指南。
2021-08-28
回顾整个刑法学发展史,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认知经历了从单一的报应刑到以报应刑为基础兼顾改造教育的预防刑这样一个发展历程,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在刑罚观上最大的分野。被处以监禁刑的服刑人员在刑满释放之后,面临着再度融入社会的问题。监禁刑的执行必须牢牢把握改造罪犯是为了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这一核心宗旨,打破监禁执行的隔绝状态,对症施策,提升教育改造的针对性。
2021-08-24
在刑法理论上有必要厘清未必的违法性认识、违法性错误以及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之间的区别。未必的违法性认识和违法性错误之间,应从作为违法性认识本质的认识的侧面来区别。处罚以未必的违法性认识实施的行为时,根据具体案情可能存在阻却责任或减轻刑罚的情况,但阻却责任的根据不是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而是缺乏期待可能性。在确定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时,应考虑行为人计划实施行为的违法严重性、会危及什么利益、放弃行为造成的损害严重性、行为是否可以推迟直至获得明确的信息时再进行,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责任被阻却。当客观上法律状态不明确、
2021-08-17
人气:3322

人气:2072

人气:1808

人气:1294

人气:1080
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
期刊人气:1071
主管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出版地方:上海
专业分类:政法
国际刊号:1005-9512
国内刊号:31-1106/D
邮发代号:4-375
创刊时间:1982年
发行周期: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见刊时间:一年半以上


影响因子:0.096

影响因子:0.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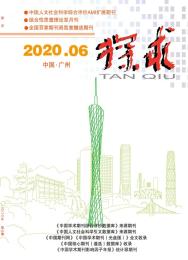
影响因子:0.580

影响因子:0.509

影响因子:0.101
400-069-1609
您的论文已提交,我们会尽快联系您,请耐心等待!
你的密码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