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卡塔西斯”作为《诗学》悲剧定义中的核心术语,其被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充满着多义变化。从其“疏泄”“陶冶”“净化”等汉语翻译语义入手,通过对其意义生成的回顾,分析其中国文域的意义建构,体现在“遮蔽”和“突显”的阐释原则,即在“宗教”意义维度的回避,以及平和协调“中庸”原则的突显。在此基础上,体察出其对功用性的侧重,并由此所造成的对审美性的忽视,为进一步理解《诗学》汉译建构,架起一座捷达而立体的桥梁。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誉为西方第一部专门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在其第六卷第七章论述悲剧功能时,提及“卡塔西斯”。“卡塔西斯”作为悲剧的核心术语,由于亚里士多德未曾给出准确的解释,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其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西方,大致可分为“净化派”和“宣泄派”,前者以弥尔顿和拉辛为代表,后者以贝内斯为代表,但仍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现有的汉译“卡塔西斯”都出自于汉译《诗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节选,主要有以下几种:天蓝译“宣洩”,[1]17傅东华译“适当之宣洩”,[2]21陈中梅译“疏泄”,[3]63缪灵珠译“净化”,[4]18朱光潜译“净化”,[5]172崔延强译“净化的目的”,[6]649罗念生译“陶冶”。[7]19七种汉译并非完全照搬原文,它们或综合西方阐释传统,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卡塔西斯”进行了汉语的重构。依据其译介的侧重点,从七种汉译中梳理出三个典型代表,分别是:罗念生译“陶冶”,侧重于思想教育;朱光潜译“净化”,立足于心理学理论;陈中梅译“疏泄”,倾向于医疗作用。
关于汉译“卡塔西斯”的研究,国内多集中于对三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其各自的优劣、得失,如:潘智彪、黄凯颖《论“卡塔西斯”的三种解说》,[8]或立足于现代性对其进行再解读,如:朱立元、袁晓琳《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现代解读》,[9]鲜少关注汉译背后的文化建构。所以,本文通过综述汉译“卡塔西斯”意义的生成,分析出其中国文化的建构,在于“宗教”意义维度的回避,以及平和协调“中庸”原则的突显。在此基础上,指出由于侧重社会功用性,造成了对审美性的忽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汉译语词如何变换,汉译“卡塔西斯”都未曾剔除其感性生成和情感实现的特质。因此,可提炼出汉译“卡塔西斯”核心意旨在于“感化”(道德清洗)和“感动”(情感慰藉)。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西方文论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这本身就是个过滤的过程。其中,无论延展或误读,都是属于中国化的一个部分。应以此来总结、反思中国文学理论应该如何更加自觉地坚持立足自身,通过批判地借鉴、吸收、消化西方文学理论的优秀成果而得到丰富发展。
一、宗教意义维度的回避
“卡塔西斯”并非亚里士多德的首创,在进入《诗学》之前,就已经在古希腊的典籍中出现并使用。在古希腊的语境中,“卡塔西斯”的含义,主要在于医学和宗教两方面。首先,有关卡塔西斯的医学作用,早在希波革拉第学派的医学著作中,就有所记录,可概述为,借助自然力或药力的效用,将体内的有害之物排出,即“宣泄”的作用。至于把有益而多余之物排出体外,则叫作刻诺西斯(kenosis)作用。[10]17其次,“卡塔西斯”也可作为宗教术语,指“净涤”或“净化”。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著名的灵魂轮回学说,认为人的灵魂要得到“净化”,才能进入和谐的神秘境界,达到不朽。“净化”的方式是灵魂接受音乐的熏陶和经历贞洁的生活而变得更加纯净。[11]
罗念生于1962年出版的译介著作《诗学》,朱光潜于1983年出版的《悲剧心理学》,陈中梅于1996年出版的译介著作《诗学》,三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对卡塔西斯的汉译给出了以下的描述:
陶冶原文作katharsis,作宗教术语,意思是“净洗”,作医学术语,意思是“宣泄”或“求平衡”。[7]159
总结起来说,“净化”一词不能理解为潜意识愿望的满足。净化只是情绪的缓和,这是一个更简单也更合乎实际的看法,是一个被弗路伊德派理论所暗示、却不是它所独有的概念。[5]192
情感的积淀,犹如人体内实物的积淀一样,可能引出不好的结果。它会骚乱人的心绪,破坏人的正常欲念,既有害于个人的身心健康,也无益于群体或社团利益。因此,人们应该通过无害的途径把这些不必要的积淀(或消极因素)渲泄出去。[3]228-229
综上所述,三种汉译或综合西方各家之说,或立足于中国文化视域,提出自己了的看法。但在他们看来,katharsis的作用对象都指向“情绪”,或隐或现的带有医学意义上的倾向,有意识地回避着卡塔西斯意义建构的宗教维度。
罗念生肯定“卡塔西斯”作为医疗术语的意义,并以此提出“卡塔西斯”在医疗意义上的另一种解释:“求平衡”。值得注意的是,罗念生认为“卡塔西斯”的情感的平衡不止是医疗意义上的宣泄,“现在我们提出另一种解释。卡塔西斯作为医学术语,除了‘宣泄’的意思外,还有‘求平衡’的意思,即求生理上的平衡,例如求体温的平衡。”[10]166文学的力量与单纯的宣泄不同,不仅可以使情感降低,也可以使得情感的力量加强,以求达到平衡。他站在社会道德的教育角度,认为观众通过反复观看悲剧,从而养成适度的情感习惯,最终的导向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由此,罗念生提出了具有东方诗教色彩的“陶冶”说;朱光潜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卡塔西斯”的作用在于,通过宣泄被压抑的潜在心理能量,从而使心情恢复舒畅平缓,“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以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12]87简言之,通过净化的作用,人的情绪得到释放,内心豁然开朗,获得一种无害的快感。与简单的情绪宣泄相比,朱氏从动态的角度描述了心理活动的复杂过程,他的讨论与其说是对“宣泄说”的驳斥,不如说是对它的修订和完善,因为二者最终都指向同一结果——情绪的缓和,生理的健康;以医学或病理学观点解释“卡塔西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德国学者巴内斯于1857年发表了Zwei Abhand lungen uiber diear is to telische Theoriedes Dramas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用医学观点解释katharsis的理论依据,确立了“渲泄论”的权威[3]230。陈中梅立足于“卡塔西斯”医疗意义的阐释历史,提出“疏泄”说,强调以一种“无害”的方式,恢复的健康的状态。
事实上,“卡塔西斯”的宗教意义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从历史语境的维度来看,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宗教、药物学和玄学、病理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分界尚不是很明确,而且他又是神学大师柏拉图的弟子,因此,理所当然,他的思想体系或多或少会带有宗教的色彩。此外,在他的著作《诗学》十七章中“例如《奥瑞斯特斯》中的‘疯狂’使他被捕,‘卡塔西斯’使他得救”,傅译本中为“涤罪典礼”、天蓝未译出、缪译为“涤罪”、罗译为“净罪礼”、崔译为“净化”、陈译为“洗净”,是明显带有宗教印记的。但是,对于“卡塔西斯”的宗教意义,三种汉译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回避,侧重于医疗的角度生成汉译。只有陈中梅在其译本附录中提及,“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是‘宗教迷’,《诗学》在追溯悲剧的起源时,亚里士多明显地‘淡化’了它的宗教背景。”[3]229“没有提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发展的宗教背景……悲剧人物固然应对自己的抉择(或决定)和行动负责,但在某些作品里,命运(moira)的制约或神的催动是导致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原因。《诗学》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3]8
二、平衡协调原则的突显
三种汉译中,“陶冶”指向培养适度情感,维持社会和谐;“净化”指向情绪的缓和,恢复日常健康;“疏泄”强调医疗作用,以无害的方式疏泄积郁。由此,可以看出,它们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但仍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庸”原则,平衡协调的突显。无论是抒发积郁,还是调节和纯化,都是在寻求一种情感的适度与平衡,以利于观赏者心理的健康与和谐,从而产生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轻松舒畅”、“无害的”快感。
陈中梅先生在论述“卡塔西斯”时,列举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认为情感的积淀会影响个人身心健康,也无益于群体或者社团的利益。这一观点的立足点在于“不加限定的怜悯和恐惧属于tolupounta的范畴,是一些会给人带来痛苦和烦恼的情感”,[2]227其中“不加限定的情感”即是违反了平和协调的原则。虽然,产生情感的机制和它的工作效能是天生的,但情感的表露和宣泄却是可以调节的。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论述了缓解病痛或不适,使人体恢复平和的某类“疗法”或“疗程”,其中,很有可能包含katharsis的作用。《政治学》第8卷第7章里,亚氏把音乐按功能分作三类,其中一类音乐可以像药物和疗法一样起净化和调理的功用。因此,陈中梅先生认为,亚氏并不否认悲剧会引发某情感。亚氏认为,情感的引发,正确的引导胜过盲目的反对,适宜的疏泄优于单纯地阻塞。因此,悲剧之所以引发这类的情感,其目的不在于崇扬,而是以适当的方式,将它们排出体外,从而恢复并保持人体身心健康的状态,即达到“平衡协调”的状态。朱光潜在论述“净化”说时,将西方关于“卡塔西斯”的“净化论”归纳为四个流派,并分析出这四个流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净化、涤除的对象以及悲剧完成净化心灵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四个流派传达的三种概念:
1.悲剧可以导致情绪的缓和,使怜悯和恐惧得到无害而且愉快的宣泄。
2.悲剧可以消除怜悯和恐惧中引起痛感的成分。
3.悲剧通过经常激起怜悯和恐惧,可以从量上减少怜悯和恐惧的力量。[5]176-177
通过分析,朱光潜认为,净化只是情绪的缓和,并将其进一步阐释为“本能的潜在能量得到了适当的宣泄”。[5]176首先,针对净化的对象问题,他认为,净化的对象指向怜悯和恐惧这类情绪。但是,这里存在着差异,即区别于悲剧所表达的情绪,这类情绪属于悲剧所激起的情绪。其次,朱光潜关于净化的过程的观点,不同于大多数亚氏的评注家。后者认为,在净化的过程中,消解了情绪所包含的痛感成分,或者是减轻了它的程度,使得净化后的怜悯和恐惧,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形式,变得更加纯粹。反观朱光潜,他认为,在悲剧与现实生活中,怜悯和恐惧属于两类不同的经验,且本能素质是祖先所传承,千百年来少有改变。因此,依照朱光潜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说怜悯和恐惧必然含有某种病态的成分,所以也就不能在严格的医学意义上来理解净化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朱光潜是在心理学的复杂动态角度,对“疏泄”进行补充和延展。除此之外,朱光潜还论及心理学上的同感概念。所谓“同感”,是认为情感一旦传达出来,就被大众分享。这种同感的反应,对情感本身也会起作用。在表现上,艺术有着双重效用,如同教徒的祷告和忏悔,一方面减轻心理负担,另一方面也呼吁着同情,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前者的快乐。综上所述,情绪通过表现,达到缓和的状态,在被分享的同时,由于“同感”作用,还得到双重缓和。这一过程,体现着“平和协调”原则。
罗念生提出的“陶冶”说,具有东方诗教的显著特点。他主张“应从亚氏的伦理思想中去求得解释”,而“亚氏的伦理学的中心思想是‘中庸之道’”: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动机下、在适当的方式下所发生的情感,才是适度的最好的情感,这种情感即是美德。[10]166-167
综上所述,“适当”“适度”这类原则,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中地位极高。罗念生认为,人们通过观看悲剧,能够养成适度的情绪,而并非是净化或宣泄不够纯粹的,或是过于强烈的怜悯恐惧之情。所以,“卡塔西斯”的作用就是使太强或太弱的情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锤炼,达到适当的强度,“使它们成为适度的情感。”[7]119-121顺着这一思路,罗念生提及《诗学》是一种对柏拉图文艺挑动情感、影响世道人心观点的回击和挑战。在柏拉图看来,情感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无理性的部分”,是应当被放逐的。而亚里士多德则对文艺的社会功用持有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在有所节制的条件下,情感也能成为一种美德,达到适度,借此获得心理的健康,可见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影响。
简言之,三种汉译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面对同一思维对象的理性审视,着眼点和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却在思维掘进深处相会,构成一个密切的链条。由此,可以得到一种启示,尽管三种汉译的用词、侧重点和价值称量、穿透力和历史延伸、思维风格和阐述形态不一样,但殊途同归,无论是罗念生,朱光潜,还是陈中梅,都一致地突显了——“中庸”原则,平衡协调,这既符合情绪恢复日常生活正常状态的要求,也符合的以悲剧为代表的文艺活动和以德性为对象的伦理学中情感的要求。
三、“知”与“思”的割裂问题
长久以来,由传统伸延至现代,由西方延伸至中国,文艺界始终探索着“卡塔西斯”的含义。在理论的旅行中,由于文化的不同,语言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文化过滤、文学误读,翻译上的“创造性叛逆”等问题。根据汉译“卡塔西斯”有意识的遮蔽和突显,可以明显的体悟出,中国文化建构的延展和过滤,所造成的功用性的侧重和审美性的缺乏。
无论是罗念生、朱光潜还是陈中梅,都一致地肯定了“卡塔西斯”的作用不限于悲剧,影响也不限于怜悯与恐惧。广义而言,从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自我实现和创造的一种主体性实践角度出发,将会发现,“卡塔西斯”作用和影响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现象,涉及了审美表现机制,包含着对审美表现性的理解和启示。
首先,艺术作为一种创造,塑造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将本质为含混不清、朦胧混沌的情绪、意象以及生命能量冲动,纳入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性和审美价值内蕴的情感模式。
其次,在文学艺术的塑造过程中,将原本属于自然的和动物性的感觉、欲念、本能冲动进化为社会性的、超生物性的人的情感,而这一过程,追本溯源,是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进行的。换句话说,使本来是混乱无序的生物性本能转而成为具有一定理性内涵和审美意蕴的人的情感。由此,原始生命冲动中潜在的、未显现出意义价值的、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因素被转换为意识到的,具有理性意味的审美情感。[13]
综上而言,站在主体性实践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卡塔西斯”这一术语,关键在于从“知”与“思”的结合角度来说明其的性质的和特点,考察其得失。所谓“知”,它的着眼点在于对象本身,基本问题是属于科学范畴的问题,探寻如何把握和认识对象本身,对象的客观规律、普遍性以及必然性等问题。[14]“思”着眼于对象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和意味,在认识对象是什么的基础上,对其意义和与主体之间关系进行叩问和思索,并且对此类问题进行体悟。因此,可以说“思”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里的问题,是人主体性的问题。
汉译“卡塔西斯”存在着“知”与“思”的割裂问题。汉译“卡塔西斯”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知”的层面、科学的层面,着力研究对象本身以及对象本身的具体现象,未能进一步的体察和领悟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意味。在“知”这个层面,罗念生倾向教育意义的“陶冶”说,朱光潜情绪缓和的“净化”说,陈中梅治疗意义的“疏泄”说,都带有明显功用性和工具性意味,都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体系,符合心理学的本能释放,符合医疗的治愈意义。然而,只有在引入作为主体的人,这一基础之上,对象才能有意义和意味,就对象本身而言,是无所谓意义和意味的。在这个意义上,汉译“卡塔西斯”存在着自我思考和体悟的缺失。“卡塔西斯”的实现是以艺术文本的境界实现为前提,在“思”的这一层面,主体性体现于,在实践过程中,经历“感化”(道德清洗)和“感动”(情感慰藉),并最终达到宁静平和,于空灵的境界中产生顿悟。由此,上升至审美层面,其背后的核心内涵应是融情,即情绪的宁静关怀和情致的超然忘返,最终创造出一个忘情和心灵感应的诱导空间。对接受者而言,将体现为一种“怡情”状态,即感性的生命介入,主客体之间的情绪通道连接为一,从而达成心理同构意义上的共鸣,如宗白华所说:“于是,人我之界不严,有时以他人之喜为喜,以他人之悲为悲。看见他人的痛苦,如同身受。这时候,小我的范围解放,入于社会大我之圈,和全人类的情况感觉一致颤动。”[15]综上所述,在“思”这一层面,汉译“卡塔西斯”存在着对美学本质和审美价值的忽视。无论是“陶冶”、“净化”、“宣泄”,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着“卡塔西斯”对于“现实”的干预。陈中梅倾向于治疗意义,强调情感的疏导和激发。观众借助于宣泄就可以减少或缓和有害情感的过多沉积,获得内心的平静。由此可见,陈译“宣泄”强调对个体的作用,停留于对个体的原始情感的上;朱光潜先生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强调“净化”一词不能理解为潜意识愿望的满足,认为“净化”只是情绪的缓和。但这一观点依旧囿于个体,停留于个体的原始情感;罗念生侧重于社会教育的功用,“陶冶”说以一种“双向调节”的形式,促进个人养成良好的情感习惯,以控制感情维持适度,最终达到维持社会和谐的目的。与此同时,和谐的社会氛围,也调节和维持着个体情感的健康。尽管“陶冶”说由对个体的原始情感塑造上升到社会整体的和谐,是一种超个体的社会情感,遗憾却局限于功用主义和纯粹的教义,仍未上升到“审美”情感层面。
汉译卡塔西斯存在着“知”与“思”的割裂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知”的层面,缺乏“主体性的思考”,着力研究对象本身是什么和对象本身的具体现象的描述和说明,至于这种现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意味,却未进一步思考和体察。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中,这一问题普遍存在,导致了这一历程,是通过阐释历史,或者借用国内外的某些观念,进而对观念本身进行思考,而并非立足于对文艺现实的具体准确把握基础上。显而易见,造成了理论的思想之花开放在空中,而不是中国的土地上。实际上,“知”与“思”是相通的,既要深入科学层面,又要深入审美层面,在把握客体的基础之上,增强主体性的体悟,将其融入中国文论的实际需要之中。
总之,三种极具代表性的汉译“卡塔西斯”——“疏泄”说、“净化”说、“陶冶”说,在译介过程中,虽各有侧重,但殊途同归,立足于中国文域的实际,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建构,即有意识的遮蔽“宗教”因素,以及突显“中庸”原则。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卡塔西斯”两个“核心成份”——“感化”(道德清洗),“感动”(情感慰藉)。与此同时,这份重构又囿于对“卡塔西斯”功用性强调,停留于个体的原始情感,未能上升到“审美”情感的层面。但,依据悲剧传入中国的历程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历史语境,“卡塔西斯”的审美意义似乎不如其功用性那样,容易被认同。应该指出,“卡塔西斯”所蕴含的文学的感性生成和情感实现特质,为理解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即“知”和“思”的结合,对客体的科学把握和主体的理性体悟。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天蓝,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2]亚里士多德.诗学[M].傅东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3]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4]缪灵珠.缪灵珠美文译集(第一卷)[M].章安祺,编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M].苗力,编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潘智彪,黄凯颖.论“卡塔西斯”的三种解说[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96-101+150-151.
[9]朱立元,袁晓琳.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现代解读[J].天津社会科学,2008,(02):116-120.
[10]罗念生.罗念生全集(卷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1]徐媛.“卡塔西斯”的古典内涵和现代启迪[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4.
[1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3]王列生.“境界”与“卡塔西斯”——中西文学审美观念非恒值态实证互阐[C].广西:东方丛刊,1995:122-140.
[14]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学学术史(第四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15]宗白华.艺术生活[N].少年中国,1920-02-07.
罗雨涵,杨红旗.遮蔽与突显:论汉译“卡塔西斯”的文化建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5):109-112.
分享: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传统源远流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旧体诗词创作传统在近现代一度中断,出现了鉴赏活动与创作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2024-03-07
21世纪初,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断,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众传媒的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交流沟通的方式,使得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越来越依赖智能媒介。
2023-11-1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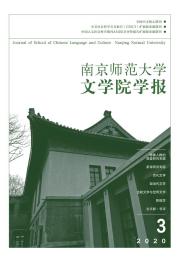
2018年,笔者基于在教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课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从尝试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申报了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资源库的师生共建及考评体系的改革实践”。最初的设想是针对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寻找有效解决课程学时短,课程内容多,学生课后阅读严重不足等问题的方法路径。
2023-10-16
童谣,即儿童歌谣。有学者认为,儿歌的古称为童谣,原因是“五四”以后中国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歌谣运动后才出现了“儿歌”这个名称,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儿语、小儿语、小儿谣、孺子歌等名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称为儿歌。实际上,更早使用“儿歌”一词的应该是周作人,他的《儿歌之研究》发表于1914年。
2022-04-02
宫体诗产生于南朝齐梁时期,与“赋”这一修辞手法在诗歌之中的广泛运用有关。南朝时期,诗人尤其注意对于诗歌技艺的探讨,包括诗体、修辞、声律等诸多方面。而关于其中“赋”法与咏物等技巧的探索,主要集中于齐梁与初唐时期,并最终形成咏物诗。宫体诗则可以看作这种探索成果的代表产物。与此同时,它又以自身独特的风格开创了诗歌中一种崭新的审美范式。
2022-01-28
《送行》作为袁哲生的文学作品,打破了单纯以时间为轴的线性叙事,未着重于送行的前因后果,而立足于送行这一过程本身,借由空间叙事使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疏离状态。本文以空间叙事学作为理论基础,从地志空间的再现、文本空间的复杂性、空间书写中的人物塑造三个方面,探讨袁哲生《送行》一文的空间叙事特点及表达技巧。
2021-09-0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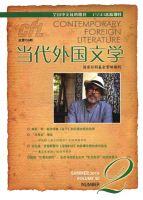
梶井基次郎的作品,具有多处描写光和影、明与暗的特色。这种明与暗并非只停留于风景描写表面,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也紧密相连。在梶井基次郎的评传中,透过他的成长也可发现在梶井基次郎的内心一直有相互对立、矛盾的两个声音在斗争着。一个便是明、一个便是暗,二者互相交织并萦绕其一生。另外,梶井基次郎曾认为明与暗是其文学主题,福永武彦等人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这样看来,明与暗不仅是梶井基次郎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解开其文学特质的重要线索。因此解读梶井基次郎文学的明暗二重性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试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浅析这一
2021-09-08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创作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它以中国革命历史为题材,主要讲述革命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通过革命认识历史,对历史进行建构与书写。在革命历史小说中,《青春之歌》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以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为题材,讲述了在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一时代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成长为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本文将从革命历史叙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体现、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结合三个方面,结合
2021-09-08
诗歌之美在于具有韵味,只有意蕴丰富、余味无穷的诗味才能让诗歌具有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杜甫的诗歌中就充满了韵味,性情中不为人知的狂味,忧患一生的苦味,鞭挞现实的辣味。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年少还是晚年,杜甫都以饱满的情感和纯熟的诗艺散发出独到的韵味。本文以杜甫诗之味的角度,分别从狂味、苦味以及辣味入手,并结合杜诗进行分析,以探求杜甫诗中之味。
2021-09-08
“忧患意识”这一概念最早由徐复观先生提出,他指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在尧舜禹时期就初现端倪。本文从学界对忧患意识的形成时间入手,通过对尧舜禹时期、夏朝、商朝时期的忧患意识进行分析,梳理忧患意识的源流,并总结忧患意识的内涵。
2021-09-08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文艺理论与批评
期刊人气:3075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艺术
国际刊号:1002-9583
国内刊号:11-1581/J
邮发代号:82-205
创刊时间:1986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一年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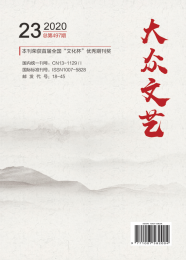
影响因子:0.270

影响因子:0.339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0.000
您的论文已提交,我们会尽快联系您,请耐心等待!
你的密码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