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公元1世纪,基督教传入埃及,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从此,在“法老文明”土壤的包容孕育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往拉开了历史的大幕。在跨越一千多年悠久的交往历史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碰撞冲突、相对和平以及团结合作的互动转换中艰难前行。当代埃及,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面临着来自宗教自身、政府层面以及外部环境的三重风险,更使得埃及宗教交往的文明进程步履维艰。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宗教自产生之初就开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埃及宗教传承历史悠久,宗教历史的延续确立了埃及的多宗教国家属性。在埃及,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穆斯林占埃及总人口90%,基督教(埃及基督教主体部分是科普特教会1)为第二大宗教,基督徒(埃及的基督徒被统称为科普特人)占埃及总人口的10%左右,正是基于埃及这样的宗教特性与宗教历史背景,使得宗教在埃及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也导致了埃及宗教交往中问题的复杂性,而且随着埃及现代化、民主化进程,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从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历史维度的切入,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埃及宗教交往中复杂的影响因素。
一、跨越千年的碰撞
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伊斯兰教建立之初向外进行宗教传播的时期,在伊斯兰教还未进入埃及之前,穆罕默德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伊斯兰教信仰,并派出大量使者,当时罗马帝国埃及总督向穆罕默德送出一份礼物和两名女奴,其中一位名叫玛利娅(Maria)就是埃及基督教徒,之后她成为穆罕默德的妾,并为其生下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1]这也成为埃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最早期的原始交往萌芽。642年,伊斯兰教以暴力入侵的方式占领埃及,并将伊斯兰教带到了当时基督教为主体地位的埃及,二者交往的历史开端就建立在暴力不平等的交往语境中,而且由于各自宗教的排他性,也注定了他们不平静的交往历史。
整个中世纪,伊斯兰教在埃及建立起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优势地位,基督教处于完全被动的弱势地位。随着伊斯兰统治中“迪米”2制度的出现,针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的限制和条件越来越严格,伊斯兰教以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单向度地展开对基督教的信仰行为的渗透,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教从政治层面的利益诱导以及紧逼政策,吸引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在欧麦尔二世时期,伊斯兰统治者一方面提高基督徒赋税水平、强化对基督教徒的各种限制和制约,另一方面对伊斯兰教徒采取免除赋税的做法,使得埃及许多基督教徒或出逃或转信伊斯兰教。阿拉伯语被定为埃及官方语言,科普特语3和希腊语被废止,统治者干涉基督教牧首选举等一系列行为,以及阿拔斯王朝针对埃及基督徒更为严厉的身份限制、强制凸显非穆斯林性,破坏教堂等行为,都使得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立矛盾加剧,暴力冲突凸显。在不断严厉和丰富的身份限制与歧视政策的压迫下,埃及基督教徒的反抗情绪已经积累到即将质变的状态,在伊斯兰封建君主残暴行径的引爆下,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对于封建王权以及伊斯兰教的激烈反抗,如果说修道院4的兴起与发展是埃及基督教宗教层面冷暴力反抗的典型方式,那么,起义等热暴力形式就成为基督教徒在世俗层面对抗剥削压迫统治、寻求公平对待的主要形式,725年、750年、831年的科普特人起义,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起义不断发生,虽然最后都被统治者血腥镇压,但是从伊斯兰教进入埃及的200年时间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不平等交往最终走向以暴力碰撞为特征的宗教对抗。
11世纪,法蒂玛王朝哈基姆统治末期以及马穆鲁克王朝时期,歧视压迫的统治路线以及严格苛刻的政治环境没有发生变化,这都导致基督教只能在更小的范围内活动,而且统治者对于宗教矛盾冲突的纵容态度,直接导致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处于冲突的激烈性和频繁性,基督教徒的人身攻击、教堂破坏成为常态,据统计,教堂从1200年的2048座减少到1600年的112座。[2]现代埃及宗教交往的传统语境没有发生实质变化,1922年,英国承认埃及为主权独立国家,埃及实现了初步独立,1923年埃及第一部宪法出台,埃及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宪法还规定了全体埃及人信仰自由,但是宪法中还保留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等内容,虽然科普特人并不承认自身作为埃及少数族群的存在,但事实上,他们的宗教确实已经处于一个国家次等的席位,伊斯兰教的优势语境和强势社会角色没有发生改变,而且随着代表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出现,使得不管从埃及的宗教领域还是社会生活领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相互的敌意和不信任情绪不断叠加,经历了短暂抗击侵略的合作之后,宗教冲突和碰撞再一次成为了二者最终走向的必然结果,在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往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历史传统中。
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到2011年历经40年,虽然埃及的现代化建设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从宗教交往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碰撞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将纳赛尔时期积累的矛盾冲突全都爆发出来,并且释放出可怕的能量。萨达特时期,伊斯兰教法在国家宪法地位的规定导致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矛盾激化,许多伊斯兰激进组织袭击教堂,而且在社会中,简单的财产纠纷升级为基督教家庭和穆斯林家庭之间的宗教冲突。[3]在科普特正教会教皇的激进思想指导下,从宗教领域开始,埃及基督教从被压迫的弱势地位开始反抗,与伊斯兰教、穆斯林不断出现热暴力冲突。穆巴拉克初期对于伊斯兰极端思想的打击和控制,以及对基督教的安抚,使得双方的激进对抗情绪被暂时稳定下来,但是时间不长,这种宗教对立、敌视甚至暴力冲突的氛围再一次回到埃及社会,而且从范围、规模以及频率都远远超过之前的时期。“阿拉伯之春”引发埃及混乱的3年时间里,埃及教派冲突不断,仅2011年埃及媒体报道教派冲突达到70起。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的暴力冲突事件数量依然在上升,而且许多社会生活问题也都最后演变为两个教派的冲突。在许多涉及宗教、民族问题上,国家政策失衡以及政府部门处理行为失当,不仅加剧了两个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敌视,而且直接导致双方关系走向文明的背离。
二、集权之下的相对和平
埃及宗教交往始终以波浪前进的历史形态而出现,并在其中凸显出政府行为与政策的重要性,在中世纪埃及,基督教在歧视、压迫的“恶政”反抗统治中波浪向下发展导致双方的暴力冲突,如科普特人起义以及修道运动的兴起,之后统治者吸取前人经验,以宽容开放态度实施善政,波浪向上发展,推动埃及宗教交往走向相对和平的共处时期,此外在宗教关系恢复期,埃及表现出强势政府,在社会混乱,宗教关系恶化时期为推动宗教交往走向文明化发挥巨大作用,这在纳赛尔和塞西政府时期表现明显。
法蒂玛王朝时期出现短暂的和谐交往进程,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之间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这得益于统治者相对宽容和开放的宗教政策以及统治理念,一定程度上维护基督教的权利和利益,而且哈里发带头参加基督教节日与庆祝活动,甚至第四代哈里发穆仪兹还改信了基督教,这些都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文明交往创建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纳赛尔时期,基督教在宗教领域得到一定的宽松政策,赛尔奉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而且遏制伊斯兰主义的泛滥,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纳赛尔威权主义下的“家长制”作风给予基督教和科普特人许多帮助,提升了埃及宗教交往中基督教的弱势地位,在他的努力下,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矛盾以及部分穆斯林对科普特人的敌视和歧视被压制下来(但没有实际解决)。但是在世俗主义政策推行下,穆斯林群体受到影响较小,而埃及土改和国有化运动使得大批科普特人被推到了埃及社会的边缘,使得科普特人政治和经济地位直线下降,许多科普特精英分子大批移民海外,这也直接导致基督教在埃及社会的影响力更加下降。
威权主义对于现代埃及的民主化建设产生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埃及威权主义对于宗教交往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埃及当专政或威权主义与一定意义上的善政相结合,宗教就能够实现相对和平的共处,而当专政或威权主义与恶政相挂钩,宗教之间往往冲突矛盾不断。不可否认,虽然废除专制制度必须先于民主过渡,[4]但是从埃及现实政治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现,理想中由西方民主模式下推翻的威权主义在埃及带来的不是更完善的社会,而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更加频繁的暴力冲突以及社会的混乱与倒退,阿拉伯之春后,埃及正在逐渐沦为“失败国家”,[5]西方民主化在埃及水土不服特性显露无疑的背景下,说明了埃及的宗教交往离不开强势和集权政府,埃及需要在威权主义体系下,良好政策范围内,政府优秀的治理能力引导下实现各方利益的协商、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6]
三、基于埃及身份认同的团结合作
埃及宗教交往碰撞中,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面对外部侵略者时表现出高度一致的埃及身份认同,13世纪初到中叶第5、6、7次十字军东征目标直指埃及时,埃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联合在一起同仇敌忾,站在同一阵营共同抵御外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进一步增进了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大众教徒的关系。
在近代以来,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英法殖民入侵,法国入侵时期,拿破仑试图保持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平衡,1805年,法国被赶出埃及,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实际统治者,阿里及其继承者的统治开始为埃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交往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采取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构建了相对平和的交往环境,废除科普特人丁税,并且以国家法律形式给予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7]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开始了40年的殖民统治。虽然英国人采取一系列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不仅分化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关系,而且从科普特人内部也采取弱化民族团结的策略,然而这都没有影响他们联合起来反抗殖民斗争的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爆发,在革命中出现了“新月环抱十字”的旗帜,而且喊出“信仰归上帝,祖国归大家”和“新月和十字万岁”的口号,科普特正教会牧师塞尔吉乌斯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布道台上呼吁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团结起来,抵御英国人殖民统治,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合作在世俗民族独立运动走向高潮。
从近代开始,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中冲突的主体地位已经发生变化,斗争不再是埃及宗教团体之间的斗争,而是针对外国殖民者的斗争。[8]但是2011年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运动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从过去对外反抗殖民的合作变为对内推翻政权的合作与互助。2011年初,“信仰归上帝,祖国是大家的”的古老标语再一次出现在埃及广场,2011年2月4日,科普特人挥舞着带有十字架纹身的手腕,保护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免受攻击,两天后,穆斯林群众蜂拥在科普特人星期日弥撒的广场以确保科普特兄弟的安全。[9]尽管我们看到的仅仅只能算作是现代埃及社会的片段图景,而非全部,尽管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及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歧视仍然存在,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互助确实真实存在。
四、埃及宗教交往任重而道远
(一)埃及宗教文明交往的本质
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10]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交往。虽然在宗教交往过程中暴力从未停歇,但是埃及国家的形成离不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团结与合作,而且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需要置身于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往中对埃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反思。
不管从世界文明交往,还是埃及宗教交往的历程来看,任何文明交往的历程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是以一种波浪、螺旋式,甚至会出现迂回式的状态而进行。首先,文明的属性不会先天存在于宗教交往中,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中的各种碰撞冲突,都没有妨碍二者试图寻找和谐文明的交往模式的决心,以及交往文明化的趋势。不可否认,碰撞在宗教交往中的消极作用,但是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趋势决定了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的文明化趋势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往历程表现出二者始终保持的开放姿态,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从未间断的互动与交往成为双方实现文明和谐交往的有利条件。其次,从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历程来看,二者敌视——暴力碰撞的状态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存在于双方之间的阻碍因素被剔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始终试图在埃及的国家身份认同中寻找双方良性、平等、积极的互动与共融。最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在基于古埃及文明的媒介中进行交往互动,他们对古埃及文化的认同也是双方文明交往的重要基石。而且从双方碰撞与交往的历程中不难发现双方相互影响,互补、互助、互动等双向关系和特征始终存在,交往的文明性有时会潜在,但是从未在历史发展中消失。5
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往历程虽然复杂而坎坷,但最后也势必将走向“交往而通”的状态。正如彭树智先生在关于美国学者斯蒂芬·儒(StephonRu)在《在对话中成长:“后9·11”世界的苏格拉底视角》关于“通状态”的理解,“通”的中心是交往而贯通,是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这是认识人类文明交往最深沉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也称为“贯通的状态”。[11]
(二)依然严峻的埃及宗教交往环境
历经2011年之后的三年,2014年,塞西政府强势执政,埃及国内宗教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这得益于国家宗教政策的相对平衡,塞西一方面强调教会在埃及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肯定了基督教以及科普特人对埃及国家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极端分子对基督教的袭击行动中,政府也给予了科普特人重视和保护,在政府的努力下,虽然埃及教派矛盾和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但是政府在缓解以及调节宗教矛盾和冲突方面的正确决策,以及2018年塞西总统继续连任,使得他的政策得以延续,这些都使得埃及两大宗教的文明交往成为可能。但是不管从埃及宗教自身,还是政府以及社会环境层面,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仍然面临着许多内外风险。
1.宗教层面。
在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碰撞很大程度上都与宗教的观念冲突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这是由于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作为天启宗教,其信仰原则具有神圣性,而宗教信徒对于信仰原则坚守的不妥协性使得宗教分歧难以弥合,当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与宗教分歧交织缠绕,就导致两种宗教交往中不可避免的敌视冲突甚至暴力行为。
从宗教的层面消解或者缓解这种宗教分歧不仅是二者走向和谐相处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埃及社会宗教交往中必然面对的风险所在。我们看到,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往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的竞争,而且这种趋势在受到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强烈,所以从埃及社会两大宗教层面来看,做好“邻居”的第一步将不是拆除篱笆并试图建造一个宗教的公共用地,而是尽可能真正表明我们是谁,并让我们的邻居在我们对着篱笆谈论时看到我们是谁。[12]强化自我理解与对对方的理解是解决“我们是谁”以及“他者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就使得双方的宗教理解需要建立在具体事项上的双向、互动式的友善行为,而且更需要以温和的姿态、而非激进的思想从各自信仰体系去建立最广泛的宗教理解基础和教徒基础,通过非语言化的形式6强调埃及社会责任以及人类终极关怀属性而非宗教分歧与指责,而这不仅是当代埃及两大宗教社会交往层面所缺失的重要内容,也是二者交往走向文明历程的重大挑战和风险。
2.政府治理层面。
宗教在埃及历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管是642年之前的埃及“基督教时代”7,还是之后伊斯兰政权统治时期,不管是埃及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埃及不仅从未出现过宗教政府,而且埃及政府始终将宗教作为统治工具试图将其进行控制,宗教则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向政府以及政策提供宗教支持,[13]这就使得在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历史中统治者(现代形象为政府)的影子始终存在,而且政府也成为二者走向消解危机、互相信任,或者加深矛盾、走向冲突非常关键的因素。从埃及宗教交往的历史来看,古代社会统治阶层对于基督教的歧视、限制等压迫剥削政策,以及在现代埃及社会建构中,科普特人权利意识觉醒与不相符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中不公平对待,以及现代政府宗教政策和管理失当行为,都造成了埃及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矛盾不断积累升级,暴力碰撞频发的局面,这在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尤其明显,政府在宗教交往层面的消极影响显露无疑。而从政府的积极影响来看,古代法蒂玛王朝短暂的宽容、开放政策,以及纳赛尔时期的宗教制衡性政策和个人威权主义都一定程度上从政府角度保证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文明交往的可能。从这一层面来看,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集权政体都成为埃及宗教交往的重要因素,而反观埃及政府建设层面,政府治理体系建设滞后,管理不完善,贪污腐败问题严重,以及纳赛尔去世后,威权政体与统治强人宗教治理能力不对等,埃及西式民主化转型失败,这都给埃及宗教交往的政府管理层面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随着塞西新强人政治登上埃及舞台,政府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埃及宗教交往的社会环境,但是关于政府民主化转型以及宗教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挑战与风险仍然巨大。
3.外部环境层面。
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碰撞与交往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首先,反抗对外侵略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能够实现团结与合作,而英法殖民统治埃及时期,二者又由于统治者的挑拨离间以及分而治之、孤立等政策,出现宗教关系不断恶化,从加利上台被杀引发的科普特人大会和穆斯林大会的召开,到整个埃及社会中充斥着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敌视,都透漏着英国保证埃及殖民统治的目的。[14]由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交往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导致二者关系也存在非常大的不稳定性。其次,随着埃及“科普特问题”引发海外科普特精英群体的激进情绪,这种情绪蔓延到国内社会,造成基督教方面的激进思想,这种激进思想又一定程度上推动基督教“以暴制暴”的对抗行为。此外,近代埃及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权等问题不断干涉埃及内政,以及西方媒体对埃及宗教情况缺乏公正和不实的相关报道,也加深了二者的不满情绪。最后,埃及境外分裂势力以埃及多元宗教教派和民族问题展开分裂活动,以伊斯兰主义为代表的埃及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基督教的敌视有增无减,以及不断试图制造针对教堂和科普特群体的恐怖袭击,这些层面的风险不仅没有缓和埃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矛盾,而且成为了阻碍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开展对话的重要因素。[15]
五、结语
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埃及宗教交往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主要概括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过去宗教交往事实中的伊斯兰教的优势地位和话语霸权,到现代埃及基督教提出更多诉求,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对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取更大权力来改变传统基督教在埃及社会的弱势地位,试图打破埃及传统社会中伊斯兰教的强势语境。第二,从最早的十字军东征,到近代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再到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干涉埃及内政,埃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情况有增无减。第三,埃及强权政府在应对全球化以及自身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遭遇的能力瓶颈,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效一度导致埃及政府崩盘,社会陷入混乱。尽管从2014年以来,塞西军政府短期内基本实现了国内和国外环境的相对稳定,但是如何平衡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宗教势力,如何在协调埃及外部环境基础上实现国内社会经济的复苏发展来缓解各方矛盾,甚至以怎样稳定的形式实现埃及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转型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都将成为未来埃及宗教交往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彭超.埃及科普特人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7:26.
[5]田文林.“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J].国家问题研究,2014(05):64.
[6]毛志浩.威权主义视野下的埃及民主转型分析[J].亚非纵横,2015(02):86.
[7]李福泉.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J].世界民族,2007(05):19.
[10]彭树智.文明交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总论部分.
[11]彭树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7.
[12]保罗·尼特.宗教对话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0,234.
[13]〔埃及〕巴其纳姆·沙尔卡维著.全球治理时代的埃及教俗关系[J].包澄章,译.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03):5.
[14]杨灏城.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第1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60.
[15]尤梅.当代埃及社会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浅析[J].世界宗教文化,2011(06):46.
注释:
1.科普特教会全称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属于东方正统教派的分支,但区别于东正教,信仰基督一性论。
2.Dhimmi(迪米),指在伊斯兰统治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的非穆斯林,即“受保护的人”。迪米人在其社群中享有自己的特殊法律,并且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是在国家层面则受到许多限制,并且不享有某些政治权利,他们需要缴纳Jizya(人丁税),而穆斯林则不需要。
3.科普语被称为古埃及语发展的最后阶段,在罗马拜占庭统治埃及时期,古埃及语与希腊语相结合形成了科普特语。科普特语不仅借鉴希腊字母,并且承袭古埃及语中的字母,但是在公元10世纪初,随着阿拉伯语在埃及各个领域的推行,科普特语在实际意义上已经脱离埃及社会,成为仅仅在科普特宗教层面使用的语言。
4.埃及修道院的兴起与当时社会苛捐杂税以及种种限制、歧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许多基督徒一方面为了宗教信仰,也有为了躲避经济、政治压迫等原因,都纷纷出走去荒芜、远离城市的地方进行苦修。
5.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碰撞与交往中,基督教接受了阿拉伯语,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许多风俗习惯既受到古埃及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对方的影响,如艺术文化、丧葬礼仪、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是如此。
6.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从起源、以及遵循的教义、教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共通性,二者的信仰体系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非语言化形式强调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科普特正教会甚至基督教,抛开他们各自的具体教义信条,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表现形式,他们之间有着必然的共性,这就是那个超自然超越人类的终极者,这从本质上来讲,他们宗教的本质与核心的东西是一致的,所表现出更多是外在和非本质的语言形式,而二者的对话和和谐共处的基础目前来看应该是放下象征体系本身的形式,关注象征对象的本质,得其“意”而忘其“字句和语言”。参见文章《Religion:InDeepConcernAboutWorldPeace》。
7.公元30年,屋大维率军征服埃及,罗马帝国统治埃及,公元1世纪,基督教传入埃及,埃及人为对抗信奉多神教的罗马统治者,埃及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开始了埃及的基督教历史(也称“科普特历史”),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统治埃及,伊斯兰教信仰体系进入埃及,之间这段历史称之为埃及“基督教时代”或科普特时代。
白韶璞.埃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碰撞与交往[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29(04):96-101.
分享:

“中和”是中国古代乐舞的审美标准,“美善”赋予了中国古代乐舞伦理特征。“中和美善”既是中国古代乐舞的精髓,也是古代乐舞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主张用富有伦理内涵的“中和之乐”引导百姓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提高他们的人格素养。探讨“和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对指导当代的艺术实践仍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2021-05-04
朝廷赐予地方神明以封号,或者将历史人物封神,列入官方正式的祀典,并在全国各地对其进行倡导与传播,这样的神明“正统化”1早已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宋代,敕封达到高潮,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真宗亲自“东封西祀”。然而,通过假借敕封以建构其“正统性”的做法并不多见。
2020-09-24
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体现着人类对生存价值的最深层探寻。中国古代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观念作为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思想内核之一,早已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中国宗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儒道佛三教并重、融合为特征的宗教精神成为古代士大夫阶层的普遍信仰形态并通过文学等形式表达和传播。
2020-09-1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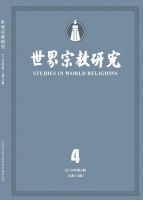
本文精选了部分宗教方面的优秀题目,供各位宗教相关工作人员参考,如需更多关于论文写作和题目的相关内容,请查阅本网站的其他文章。1、武百祥与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立2、憨山大师行迹3、印度教湿婆教派悉檀多支派后期发展阶段研究4、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原始巫术5、宋代买地券道教词语考释
2020-09-09
武百祥是近代哈埠民族工商业的知名人士,然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基督徒却鲜为人知。一直以来学界对他的关注也多放在商业贡献方面,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一篇论文专注其基督徒身份及其在基督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武百祥作为一名基督徒,对于基督教在哈尔滨的传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领导建立的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是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基督教自立运动的代表。
2020-09-03
高校民族宗教工作是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担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责任,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引导不仅局限在专业知识、实践能力、道德素养方面,更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以及理想信念的确立、优秀文化的传承、科学精神的养成、美好心灵的塑造等方面。
2020-08-1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既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清晰判断,也是对我国历史性变革的科学揭示。宗教工作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自然离不开对整个社会发展态势的科学把握,而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方位,也必将成为我国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引。
2020-08-13
广西西南有崇左市的凭祥、宁明、龙州、大新,防城港市的东兴、上思,百色市的那坡、靖西共8个县(市)与越南的广宁、谅山、高平3省接壤,边境线长1020公里,属典型边境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壮族人口比例高达80%以上,辖区内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三大宗教及不同民间信仰存在。
2020-08-13
在新形势下,随着招生政策、教育资源以及交通、通讯等的发展,地方高校的少数民族师生人数不断增长,宗教对地方高校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而给地方高校的统战工作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挑战。为此,同时也适应大统战格局自身建设的需要,在地方高校进行构建民族宗教工作联动机制的探索也就提上了日程。
2020-08-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我国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笔者在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践,梳理出高校宗教工作的三个特点和难点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2020-08-13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世界宗教文化
期刊人气:1434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宗教
国际刊号:1007-6255
国内刊号:11-3631/B
邮发代号:82-267
创刊时间:1980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1年以上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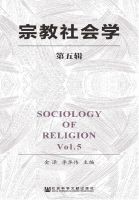
影响因子:0.000
您的论文已提交,我们会尽快联系您,请耐心等待!
你的密码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