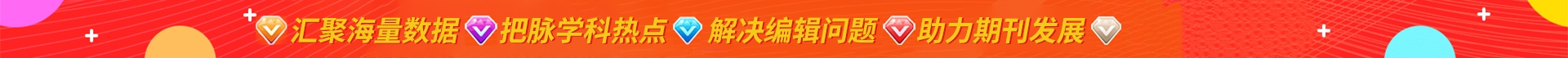
摘要:人体共生肠道微生物是一个动态系统,在宿主生理的各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免疫成熟、新陈代谢、组织发展等,但同时也能诱发或促进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乳腺癌是世界范围内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呈迅速增长的趋势。近年来乳腺癌与肠道微生物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本文基于肠道屏障、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及脂质代谢三个方面对肠道微生物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进行阐述,以把握乳腺癌的发展动向,为乳腺癌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在世界范围内,2018年新诊断出的女性乳腺癌病例达到210万例左右,几乎占女性癌症病例的四分之一,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也是导致女性死亡的重要原因[1]。据估计,全球20%的癌症与肠道微生物有着密切联系[2,3],近年来关于肠道微生物与乳腺癌相关性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人体内的微生物超过100万亿个,编码的独特基因是人类基因组的100倍[4],与宿主之间呈多层面且双向的关系[5]。宿主通过多种行为调节其微生物群的组成,但同时微生物群也可以很好地调节寄主的生理机能[6]。大多数定植于人类肠道中的肠道菌群形成共生体发挥作用,预防病原体入侵、预防肿瘤发生、参与营养物质和毒素代谢等。共生群处于微妙的平衡中,一旦肠道菌群生物量或多样性发生改变进入“失调”状态,就可诱发乳腺癌等宿主疾病进程[7,8]。
在1990年,Mineli等[9]通过比较绝经前乳腺癌患者与正常女性粪便样本中的肠道菌群观察发现,两者在大肠杆菌、需氧链球菌、乳酸杆菌及非发酵菌的数目上具有显著性差异。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肠道微生物与乳腺癌的相关性研究步入了新阶段。Goedert团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肠道菌群与乳腺癌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α-及β-多样性比健康对照组减少,且梭状芽孢杆菌的相对丰度增加[10,11,12]。基于Goedert团队建立的生物数据库,Miko团队[13]则发现I期和II期乳腺癌患者肠道菌群种类显著下降。Banerjee团队[14]研究发现每种乳腺癌类型患者都有独特的肠道微生物寄生特征,如三阴乳腺癌和三阳乳腺癌患者,而ER阳性和Her-2阳性患者具有相似的肠道微生物模式。根据上述研究可得,乳腺癌患者较于正常健康者肠道菌群种类及多样性改变,且不同分期及不同类型的乳腺癌具有各自独特的肠道菌群特征。文献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与乳腺癌的相关性涉及诸多作用机制,本文基于肠道屏障、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脂质代谢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总结,为乳腺癌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策略。
1、肠道屏障
肠道菌群参与形成一种由物理、生物、免疫与化学多种功能共同构成的屏障(图1),参与食物消化、免疫激活等过程,作为内在化的环境因素,与包括乳腺癌在内的人类多种疾病相关[15,16,17]。
图1肠道屏障
肠道黏膜细胞间连接通过连接复合物调节,其中紧密连接(TJs)、附着连接(AJs)和桥粒三个复合物最为重要[18]。肠道微生物寄居于肠腔或定植于肠黏膜表面构成生物屏障,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微生态系统。屏障完整性的破坏通常发生在各种各样的病理过程中,这可能导致菌群失调和致病菌易位,并增加肠道通透性,促进细胞中的代谢产物、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通过受损的肠黏膜进入血液。Russo等[19]通过临床试验发现乳腺癌可引起肠道通透性改变。Xue等[20]则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乳腺癌可减少TJs蛋白表达,促进细胞代谢产物D-乳酸和细胞内酶二胺氧化酶进入血液,并降低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比值,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
作为腔内内容物和潜在的免疫系统之间的屏障,肠道免疫屏障主要由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及细胞因子等构成,相互调节,维持免疫平衡[21]。共生的肠道微生物群、黏膜免疫球蛋白分子(IgA)、存在于内在固有层的先天和适应性免疫细胞等多个因素均有助于增强肠道屏障的功能[16]。ChungH等[22]实验证明肠道微生物通过刺激肠道次生淋巴器官集合淋巴结和肠系膜淋巴结中T细胞的活化与增殖影响肠道免疫屏障功能。Goedert等[12]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乳腺癌病例可显著降低肠道菌群α多样性并调节IgA-阳性及阴性菌群的组成,证明乳腺癌可导致肠道微生物在免疫识别菌群组成上形成差异。
肠道屏障具有高度动态性和对内、外源性刺激的反应性,菌群失调引起的持续性炎症反应可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破坏其完整性,且影响后续的药物治疗[23,24]。因此,肠道稳态与肠道屏障的构建和肠道屏障受损后肠道菌群易位密切相关,多微生物与宿主和平共生取决于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2、炎性反应和免疫应答
乳腺癌的发生与慢性、持续性失调的炎症密切相关。肠道微生物可促进中性粒细胞产生、诱导调节性T细胞(Treg)增殖分化等,通过减少促炎因子的分泌和炎症细胞的产生,下调全身炎症指数,促进和校准免疫系统的各个方面,抑制乳腺早期癌变过程。免疫系统的成熟可维持与高度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落共生,另一方面,微生物可诱导慢性炎症、激发不受控制的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而促进乳腺癌发生、复发及转移。
中性粒细胞作为先天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证明与乳腺癌的病情进展相关。在I、II、III期乳腺癌的研究中,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超过2.5的患者10年复发风险是小于2.5的患者的4倍[25],且中性粒细胞可受肠道微生物的调节[26,27]。Clarke等[28]发现肠道微生物缺失可影响血清和骨髓中中性粒细胞的功能。Lakritz等[29]用具有乳腺癌易感性的靶向致病性肠道微生物感染小鼠,发现病变以中性粒细胞广泛浸润为特征显著影响乳腺等远端组织的癌变进展,提示针对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中性粒细胞相关免疫应答可影响乳腺癌的病情进展。
免疫编辑和免疫逃避是乳腺癌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包括CD8+T细胞耗竭和Treg细胞功能增强。Erdman等[27]提出一种致病肠道菌群诱导肠外组织癌变模型,认为致病性感染过程中受损的肠道上皮细胞可导致肠道微生物易位,诱导乳腺等远端组织癌变,而Treg细胞有助于恢复肠道上皮稳态。但也有大量实验发现,Treg细胞在乳腺癌患者外周血和肿瘤组织中呈高表达状态,且可能通过抑制T细胞对外来和自身抗原的免疫应答促进乳腺癌的发展。此外,T细胞可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如IL-4、IL-10、转移因子等,这些因子在体内可促进免疫活性细胞的增殖,强化机体的免疫应答和炎症反应[30,31]。Rutkowski等[32]证实乳腺癌患者中存在着肠道微生物、IL-6以及T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Toll样受体5(TLR5)依赖的共生肠道微生物可促进IL-6分泌,导致γδT细胞抑制抗肿瘤免疫,促进肿瘤恶性发展。朱佳等[33]发现绝经后乳腺癌患者和绝经后健康对照者肠道差异细菌假单胞菌与Th/Ts呈正相关,且埃希氏菌属的丰度增加了4倍。肠道内埃希氏菌属的黏附侵袭可以引起体内TNF-α、IL-6、IL-8炎性因子的增加,这些炎性因子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34,35]。
随着对肿瘤免疫治疗认识的加深,靶向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体-1(PD-L1)等检查点抑制剂与肠道微生物的研究备受关注[36]。关于PD-1抑制剂治疗乳腺癌的研究尚在进行中[37],目前正在进行的KEYNOTE-012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非随机Ⅰ期临床试验,现有数据表明PD-1抑制剂派姆单抗对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明显,总缓解率约20%[38],阿特珠单抗的应答率达到19%[39]。PD-1/PD-L1治疗与乳腺癌及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尚未有文献报道。但Routy等[40]用对PD-1检查点抑制剂敏感的非小细胞肺癌、尿路上皮癌、肾癌患者粪便中的肠道微生物移植到无菌或经抗生素治疗的小鼠肠道内,改善了免疫抑制剂的抗肿瘤效果,提示肠道微生物可能产生“稳态”的共聚体,改善癌症的免疫监测。因此,基于肠道微生物探讨免疫抑制剂对乳腺癌的治疗作用以及降低其耐药性是可行的。
肠道微生物是一种重要的抗原,可刺激肠道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发育成熟,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物质可以调节其免疫反应,参与肠道局部甚至全身的免疫调节[41]。而这些淋巴组织在进化过程中扮演着一种复杂的平衡角色,既可体现保护性免疫反应作用,又可发挥抑制性免疫作用。
3、脂质代谢
脂肪细胞分泌的信号分子和代谢产物,尤其是处于肥胖状态的组织和脂肪细胞,被认为是乳腺癌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或间接刺激肿瘤抗凋亡作用、细胞生长、血管生成和迁移等过程[42]。乳腺癌细胞通过糖酵解和线粒体氧化为自身提供能量,除此之外,其他代谢途径在乳腺癌中也发生上调,如脂肪酸代谢、胆固醇代谢等。肠道菌群是内环境因素的组成之一,主要通过产生代谢物进入生理或病理循环并到达靶细胞发挥作用调节寄主的机能[43]。脂质代谢紊乱可影响双歧杆菌、拟杆菌、肠杆菌等菌群的构成比,同时肠道菌群失调可加重脂质代谢功能失调[44,45,46]。
脂类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肠道菌群可以调控诱导脂肪细胞因子,影响甘油三酯代谢相关因子和酶类的活性[47]。脂类分解启动脂肪细胞释放大量的游离脂肪酸(FFAs),破坏整个机体的脂质平衡。高水平的FFAs通过传递生成促肿瘤信号来促进乳腺癌进展[48]。肠道细菌分解发酵饮食中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纤维形成各种发酵酸,主要是丁酸盐、丙酸盐等短链脂肪酸(SCFAs),相较于中长链脂肪酸在体内更容易被氧化,参与机体免疫、黏膜屏障完整性等多个过程[49]。Kirkup等[50]通过实验发现服用抗生素后小鼠粪便中微生物来源的短链脂肪酸丁酸盐减少,可能有助于加速肿瘤的生长;并通过临床试验发现乳腺癌患者常规使用抗生素头孢氨苄后肿瘤的生长也受到了显著影响,产生丁酸盐的Odoribacter和Anaeotruncus菌属生物量显著减少,强调了肠道菌群在乳腺癌脂肪酸代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胆固醇代谢的变化也可视为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之一[51]。胆固醇代谢产物27-羟基胆固醇作为一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可以激活内质网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52]。Li团队[53]通过Meta分析得出食入过多的胆固醇可增加乳腺癌风险,PeltonK团队[54]通过动物实验证明血浆中胆固醇增多可引起小鼠乳腺癌生长,提示了高胆固醇血症可促进肿瘤生长。肠道菌群是体内胆固醇平衡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春燕等[55]实验证明无菌小鼠肠道中胆固醇吸收率下降,并伴有宿主脂质代谢基因的改变。但是,目前肠道菌群相关的胆固醇代谢多用于心血管、肝胆疾病的研究,与乳腺癌发病风险的相关性有待后续研究探讨。
因此,脂质作为活化脂肪酸氧化和构建致癌脂质信号分子的底物,可通过肠道菌群介导参与乳腺癌的生长和进展,而乳腺癌细胞可通过直接或间接与脂肪细胞相互作用或调控脂肪代谢物而进一步增殖分化、转移种植[56]。
4、展望
乳腺癌是免疫监视失败后的产物,往往与遗传变异、免疫反应、炎症介导、代谢紊乱等多个因素有关[57,58,59]。目前乳腺癌的病因机制尚未完全揭示,肠道微生物的改变可在多个层面上与乳腺癌相关,包括肠道黏膜屏障、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脂质代谢等,抑制和促进作用共存,具体作用取决于肠道微生物的组成、丰度及多样性。
肠道屏障功能失衡是乳腺癌可能的发病机制之一,此理论推动了肠道屏障修复疗法的发展。以靶向修复肠道上皮屏障为治疗目标,通过肠干细胞的分离、扩增和移植促进上皮细胞的修复。许多通道上的肠系基因表达还没有详细的表征,为肠系干细胞的移植提供了可能,例如Lgr5+肠干细胞扩展和移植后可表现出癌细胞增殖的特性[60]。基于肠道菌群,作用于肠系干细胞、连接蛋白、黏膜分泌免疫蛋白等多个靶点,是否可减缓癌症进程仍需要大量实验以证明其在乳腺癌中的疗效。
免疫治疗作为乳腺癌研究的热点,是除手术、放化疗、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之外一种能潜在提高乳腺癌患者预后的治疗方案。PD-1/PD-L1通路在维持外周T淋巴细胞耐受和调节炎症方面发挥着微妙的作用,主要在三阴性乳腺癌中显示潜在的反应。Wang等[61]将健康者的粪便菌群移植到PD-1治疗后患有重度结肠炎的癌症患者体内,患者腹泻等症状改善;课题组通过收集肠道微生物移植前后患者的粪便样本,发现移植后肠道菌群的保护性微生物得到恢复。此研究提示肠道菌群可作为一个突破点,引发缓解乳腺癌并发症和治疗副作用的新思路。
脂肪细胞作为乳腺肿瘤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人体能量代谢和脂质相关致癌信号分子的底物,与乳腺癌细胞之间存在着直接及间接的相互作用,累及肿瘤起始、增殖、存活、侵袭和转移整个癌症过程,多样化的脂质代谢重塑、致癌信号因子分泌也参与其中。脂肪细胞参与各种乳腺癌治疗的抵抗机制,成为可能的治疗障碍。肠道菌群作为脂质代谢的重要参与者,肠道菌群及其介导的脂质代谢产物具有调节与抗癌药物相互作用的潜力,但仍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或临床试验。
目前,大多数实验表明,肠道微环境中存在特定微生物可影响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但仍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试验和科学实验以获得更为准确的结论。深入探究乳腺癌与肠道微生物的作用机制,有利于突出肠道微生物的重要性,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稳态从而促进新型乳腺癌预防和治疗策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7]李瑞,李小双,桂春爽,等.肠道屏障功能与疾病发生关系的研究进展[J].中国当代医药,2018,25(23):37-41.
[55]钟春燕.菌群及巨噬细胞脂质分解在血脂调节中的作用与机制[D].重庆:第三军医大学,2016.
谢璐,万华.肠道微生物与乳腺癌发生发展关系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J].现代肿瘤医学,2020,28(21):3806-3810.
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编号:18ZR1440300).
分享:

磁共振成像(MRI)在评估软组织病变,较钼靶与CT有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广泛应用与新辅助化疗效果的评估[1,3],近年来随着影像组学的发展,不仅可从常规的影像学图片上得到肉眼能够识别的病灶体积、大小以及形状、信号,并区分其与周边组织的不同特征,而且还能够观察到肉眼难以看到的高阶特征和纹理特征[4,5]。
2025-08-29
乳腺癌首诊时已有10%左右的患者发生远处转移,而此类患者5年内生存率不足20%,故针对晚期乳腺癌患者来说,精准、高效的治疗方案直接关系患者预后与生存质量[1]。晚期乳腺癌治疗方案以多线治疗为主,诸多患者已经存在多种耐药性,因此针对晚期乳腺癌患者,在化疗基础上联合其他药物共同作用尤为必要。
2025-08-25
相较右侧乳房,左侧乳房更加靠近心脏,因此,在左侧乳腺癌患者IMRT计划设计中,如何最大程度控制心脏及LAD剂量显得尤为重要。深吸气屏气(DIBH)技术可扩张左侧乳腺癌患者双肺,使其心脏向后下方移动,从而远离胸壁,降低心脏受照剂量,其心脏保护作用已得到临床实践认可,被常规推荐用于左侧乳腺癌的放射治疗中[2]。
2025-08-25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正常乳腺细胞转变成恶性细胞并发生转移过程中,细胞间黏附降低,从而表现出一种有益于恶性细胞变动的表型并摆脱周围组织的约束。当上皮细胞受到环境刺激时,就会拥有间质表型和功能,此过程称为上皮⁃间质转化(EMT),即正常组织变换成恶性肿瘤组织。
2025-08-12
在众多癌症当中乳腺癌具有高发特征,并且是引发全球女性癌症死亡的主导因素[1]。因检查的大量普及以及诊断方式的持续优化,使得更多乳腺癌患者被有效检出,但也从中了解到每年均存在大量新发乳腺癌患者,并且该疾病开始向年轻女性群体发起进攻,使得女性生理方面以及心理方面均受到负面干扰。
2025-07-22
乳腺癌作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临床上呈现出多种组织学类型和分子亚型。其中,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breastcancer,TNBC)由于缺乏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表达从而缺乏有效的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且具有较高的侵袭性,导致其复发率较高,给治疗和预后带来挑战[1]。
2025-07-20
乳腺癌作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对女性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乳腺癌病例高达226万例,超过肺癌,发展为第一大癌症,并且好发于45~50岁的女性群体[1-2]。
2025-07-18
当归补血汤为补养气血的经典方剂。该研究基于乳腺癌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症的病机,适当加味,以补气养血、健脾和胃、填精补髓为基本治则。方中重用黄芪补气升阳,益气固表;合党参补气养血,助黄芪行补气之功;茯苓、麸炒白术两药合用,补脾益气、健脾和胃;佐少量当归补血活血,使补而不滞,与黄芪配伍,共行补气生血之功。
2025-07-1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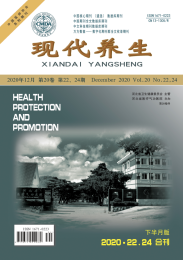
乳腺癌是一种常发于乳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多伴有腋窝淋巴肿大、乳头溢液以及胀痛等症状,在发病初期极易被忽视。据相关研究显示,乳腺癌已成为全球第五大癌症死亡原因,占女性癌症病例的24.5%,且死亡率为15.5%。宋安平研究认为,康复训练对乳腺癌患者的术后康复应用效果较好。
2025-07-08
目前靶向治疗、放化疗及手术是治疗乳腺癌的主要手段,其中乳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通常为手术,临床采用的改良根治术可直接切除肿瘤来治疗病情,但该术式对身体的创伤较大,会造成乳房缺损,影响患者的乳房美观度。保乳手术是在患者有保乳意愿的前提下完整切除乳房内的肿瘤,经病理检查证实达到切缘阴性,则保乳成功。
2025-06-1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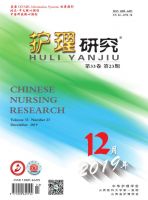
人气:18449

人气:17867

人气:17238

人气:16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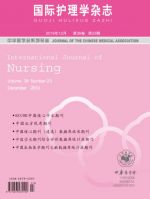
人气:16325
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癌症进展
期刊人气:4982
主管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医学
国际刊号:1672-1535
国内刊号:11-4971/R
邮发代号:80-243
创刊时间:2003年
发行周期:半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见刊时间:10-12个月


影响因子:1.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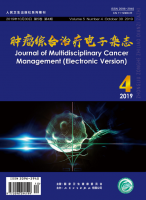
影响因子:2.876

影响因子:0.8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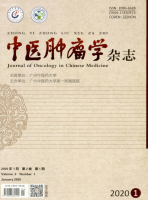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2.153
您的论文已提交,我们会尽快联系您,请耐心等待!
你的密码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看!